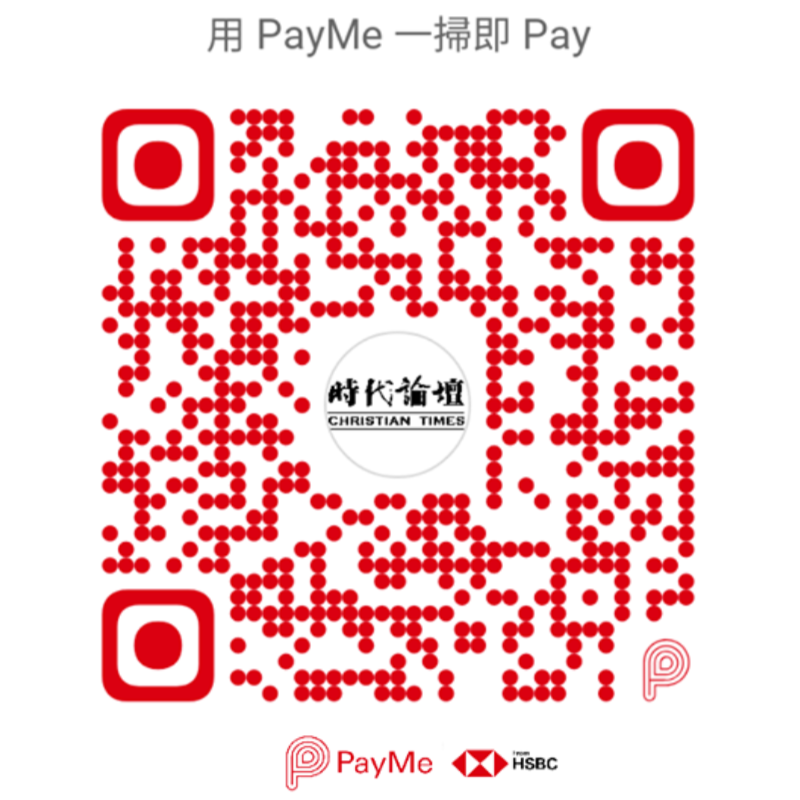本文為作者於三月六日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抗爭與靈性」講座講稿。
這三年來,時局劇變,社會撕裂,對許多人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創傷,這些創傷積累交疊而成的刺痛的記憶,該如何面對?該如何醫治?
黃絲帶信徒的刺痛記憶很多,和平理性的雨傘運動無疾而終,政府寸步不讓,政改胎死腹中,命運無法自主,前途一片灰暗。愈是有理想、有熱情的年輕人,經歷的打擊就愈大,李波事件令他們目瞪口呆,肖建華被失蹤更不可思議。大學校委會淪陷,監警會變天,廉署大地震,社會彷彿失去了一切制衡的力量。立法會選舉結果出來,曾經短暫興奮,但DQ風波加人大釋法,令他們的心沉了下去。行政長官選委會誔生前夕,梁振英宣布不連任,他們再次短暫興奮,然後是另一次的失落,民意從來不是決定性因素,永遠敵不過權勢加謀略。
藍絲帶信徒的刺痛記憶也很多。一場雨傘運動,令他們成為年輕人眼中的頑固保守勢力、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感到被誤解、被憎恨、被標籤。看到元旦旺角街頭的騷亂,示威者掟磚縱火,他們覺得這個城市很陌生,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香港。聽到本土派議員的「港獨」宣言,以及侮辱中國人民的宣誓表演,他們憤慨激動。七警案裁決出來,全部入獄兩年,他們大惑不解,質疑法院不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彷彿都不可信任,議會只是沒完沒了的拉布鬧劇,政治只是不講道理你死我活的鬥爭。
每年每月的新聞片段,都帶來新的創傷,都在挑動刺痛的記憶,惟有掩臉不看,才有片刻的寧靜。但就算不看不想,這些刺痛的記憶還是會閃現腦海,在最措手不及的時候突襲心田。
克羅地亞裔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是德國殿堂級神學家莫特曼的入室弟子。一九九三年,南斯拉夫分裂,內戰爆發,塞爾維亞戰士屠殺克羅地亞人民,強姦婦女,焚燒教堂,大量無辜平民被送進集中營。沃弗在杜平根大學跟莫特曼做研究,為學生講授「擁抱敵人」的信息,莫特曼站起來質問他,你可以擁抱那些塞爾維亞戰士嗎?這個問題迫他寫出了《擁抱神學》(The Exclusion and Embrace)這部有血有淚的著作。
克服刺痛記憶的三股力量
在《記憶的力量》(The End of Memory)一書中,沃弗憶述一九八三年他被南斯拉夫政府徵召入伍,當時南斯拉夫仍然是共產主義鐵幕國家,由於他娶了美國人做太太,又是基督教神學家,在共產政權眼中是典型的間諜、顛覆份子,軍方持續多個月對他實施監控、竊聽、刺探、陷害,然後是無窮無盡的盤問,要求他承認一些當局已認定的所謂犯罪事實,威脅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軍事法庭隨時判他八年監禁,他感到恐懼、無力、絕望。
密室訊問的刺痛記憶,鞭策他思考,基督徒如何面對迫害的創傷記憶?如何面對記憶中的迫害者?如何面對記憶中那無力、無助、無望的自我?沃弗指出,就算人刻意淡忘,刺痛記憶仍會主動探訪。有人嘗試把刺痛記憶整合進自己的生命故事,賦予某種正面意義,例如令自己變成熟堅強,或者更體會到基督受苦,但有些創痛記憶是不可理喻的,是荒謬絕倫的,是黑不見底的、是不可整合的。這些刺痛記憶可以打碎邪不能勝正、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基本信念,可以挑起仇恨和報復的原始衝動。
《記憶的力量》提出,要克服刺痛的記憶,醫治受傷的記憶,惟有倚靠三股力量,其一是捉緊基督徒乃蒙神憐愛的兒女這個新身份,以此作為安身立命的依據,拒絕讓創傷進佔生命舞台的中心位置;其二是捉緊基督復活令信徒生命不斷湧現新的可能,讓我們的未來不再被過去的經歷主宰,得以重燃盼望;其三是捉緊基督的十字架,將創痛與仇敵的回憶,置於基督十字架的神聖記憶之下,一起經歷饒恕與轉化。讓我以自身的經驗說明這三點。
我的刺痛回憶
二〇一四年二月廿六日早上,我在鰂魚涌海濱公園外泊了車,預備到常去的茶餐廳食早餐,之後返柴灣公司上班。當時我站在車邊,低頭收拾車中雜物,忽然,我感到背部被硬物撞擊,雙腿發麻,我抬頭一看,見到一個戴了頭盔穿深色衣服的男人,跳上一架電單車後座,前座有另一個戴頭盔的人,迅速將電單車駛離現場。我覺得有水滴在手上,低頭一看,看到鮮紅的血滴在手心,我知道自己受了傷。我感到雙腿麻軟無力,便坐在地上,拿出手提電話,撥999呼喚白車,對方問我在哪條街,我答不出,不知道街道名字,唯有描述街上標誌建築,終於令對方確認我所在位置。
收了線後,我感到背上濕濕的,知道出了很多血,為了減慢流血,我整個人躺在地上,我看到有去公園的市民路過,圍上來問我是否需要幫忙報警,我看到天上的雲,感受到微風,隨即聽到救護車的聲音。在白車上,我告訴救護員太太的名字和手機號碼,請他通知她。救護員把我推進急症室,醫護人員開始撕爛我身上衣服,方便檢查傷勢,我感到傷口劇痛,忍不住大聲喊痛,醫生怕我掙扎妨礙他做全身掃描,決定把我麻醉,在失去知覺前,我聽到的最後一句話,是有位護士大聲說:「我看到他的內臟。」
這一段鮮血寫成的記憶,我相信在我餘下來的人生都不會淡忘。我知道自己是無辜的,我完全不明白為何上帝容許這樣殘暴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住了五個月醫院,在醫院裡長期臥床,之後坐輪椅、拿柺仗,戴腳套,像小孩子一樣重新學走路,之後做了三年物理治療,至今仍未能跑未能跳。我應該如何面對遇襲受傷這段刺痛的記憶?
愛與恩典的包圍
做完手術後,在深切治療病房留醫,全身插了許多喉,盧龍光牧師來探我,在床邊為我祈禱,我清楚記得他的禱告內容,是求神讓我逐漸明白,發生這件事為要讓我學會怎樣的人生功課,我覺得盧牧師講出了我心底的呼求。我信主三十多年,和神有過許多深刻的交往,我確信神是公義的、慈愛的、全能的掌管我生命的主,雖然我不明白這個苦難為何出現,但我相信祂對我有美好的心意,祂不會「整蠱」我,因為我是祂鍾愛的兒女,祂保守了我的性命,祂必然會引導我。當我為盧牧師的祈禱說阿們時,我是用上全部心力,去宣認、確信、堅持,我是上帝憐愛的兒女,以這個身份作為我生命的中心點,我不容許莫名的苦難主宰我的生命。
當我這樣祈禱以後,我每天都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差遣許多天使來守護我、扶持我、安慰我,讓我看到盼望,看到生命裡許多新的可能。我太太堅持每晚在病房睡摺床陪我,她說受傷當天許多相識多年的朋友趕去醫院,陪她等消息,她彷彿看見一個又一個天使飛下來為她加力。我女兒從海外飛回來,除了給我一個擁抱,還在我的iPod上錄製了幾個音樂清單,讓我按著做運動或休息等不同需要來聽。許多醫護人員來照顧我的時候,眼神裡流露真切的關懷,許多不相識的人在醫院的走廊主動打招呼,送上問候和祝福。病房窗外遠山上的翠綠,近處的樹蔭,以及穿透林蔭灑進室內的陽光,都提醒我神的愛與恩典就在身旁,這些愛與恩典包圍著我,令仇恨、憤怒、恐懼這些創傷後遺無法進駐,讓我免受苦難記憶折磨。
我在醫院裡認識了兩位院友,一位因為大腿腫瘤阻礙血液流通,被迫切去一腿,戴義肢學走路,另一位做了化療,頭髮脫落,挺著虛弱的身體做物理治療,我們在復康路上互相鼓勵,定期聚會,手機短訊打氣,直至他們相繼離開這個世界。我經歷了以往在報館跑新聞寫評論無法體會的,人與人之間在生死邊緣的相知相遇,在疾病痛楚煎熬下領受上帝的恩典慰藉,我看見一個新的世界,走進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發現基督
二〇一五年夏天,涉嫌傷害我的兩名被告人上庭受審,我要出庭作供,再次重溫遇襲受傷的每個細節,並要接受被告律師盤問,我內心感覺到壓力,迫切向上帝禱告,但其實不知道該怎樣祈禱,想了許久,終於決定,只求一件事情,求真理的聖靈在法庭內運行,彰顯公義。在步入法庭那一刻,我再次祈禱,我問主耶穌,祢會陪我一起進去嗎?我清楚知道,祂不會撇下我,約翰福音十五章記載,主耶穌承諾門徒,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只要我們願意常在祂裏面,祂也常在我們裏面。在法庭作供時,我並不孤單。
作供完畢後,我感到很疲倦,我看了大量現場的圖片,地上的血跡,涉案的證物,而且傷害我的人就坐在對面,容貌看得一清二楚,不像過去只是一個背影。如果不是有耶穌基督陪伴同行,我不知道能否面對。經歷了在法庭與基督一起重溫受傷記憶,我忽然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遇襲受傷那一刻,在流著血等候白車那時候,基督原來也在我身旁,只是我沒看見沒為意,其實祂一直都在我身邊。這個發現,改變了我對苦難的記憶,令我不再懼怕。
審訊結束,陪審團把兩名被告定罪,法官判他們入獄十九年,最高刑罰是二十年,公義像正午的太陽彰顯。我知道來採訪的記者一定會問,怎樣看這兩個人?會不會原諒他們?我知道耶穌基督的教導,我們要愛仇敵,要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但我內心有掙扎,因為他們選擇不認罪,他們根本不承認有傷害過我,自然亦不覺得需要我寬恕,這樣,我去考慮寬恕他們是否多餘?這寬恕能否發生作用?
刺痛記憶與十字架神聖記憶
我向在神學院教書的朋友江丕盛請教,我問他是認錯先於饒恕,還是饒恕先於認錯?他很快回覆我,根據基督教信仰,是饒恕先於認錯,因為耶穌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還未承認自己有錯、需要饒恕的時候,就為我們死在大字架上,饒恕了我們。得到丕盛的印證後,我內心再無顧慮,我向來採訪的記者說,我寬恕了他們。講了這句話之後,我心裡感到輕省,刺痛的記憶被十字架的神聖記憶籠罩覆蓋,不再刺痛我的心,我從此無牽無掛,享受活在愛中的自由。
今天,我常常回到鰂魚涌海旁,在那裡吹風、看海、散步、飲茶、食飯,不是因為我淡忘了刺痛的記憶,而是因為我在那裡與基督相遇,我的生命被基督改變。
各位,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邀請耶穌基督與你同行,一起重溫刺痛的記憶,藉著禱告,把傷痛和造成傷痛的人與事,一併帶到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下,我相信你也能經歷復活基督的大能,藉祂捨身的愛和恩典,心靈得醫治,記憶被轉化。假如你經歷到這樣的醫治和轉化,盼望你能幫助主交託你牧養的人,不論黃絲藍絲信徒,都得到醫治和轉化。
(分題由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