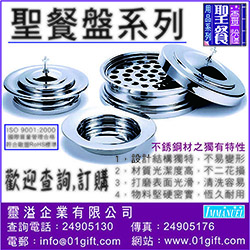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中國的精英們都想當殉難的耶穌,成為舉世矚目的大英雄。但是他們不願意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而是釘了一會兒就被扶下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走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或叫有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1
這段說話,是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中國歷史教授白杰明(Geremie Barme)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對劉曉波說的。劉氏對此深表認同。劉曉波的認同,可以理解成這種「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也是劉自身的寫照;但更重要的是,當劉曉波經歷「六四」後,他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反省及超越。本文嘗試介紹劉曉波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至九十年代初的思想世界,特別是他對基督教的觀點,藉此展現劉曉波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身分,其思想與中國現實處境間的關係。
批判傳統的十字架
這一切得把時鐘撥回到一九八○年代。改革開放令中國社會逐步走出文革的陰魅,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反省及探討中國文化的未來,形成所謂「文化熱」。這場熱哄哄的文化熱,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對思想文化的探索,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政治意義。毋庸置疑,劉曉波在這場「文化熱」中,是個絕不能繞過的代表人物。
劉曉波,一九五五年出生,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在農村插隊。一九八二年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師大中文系取得博士後,留校任教。劉在中國知識界受到關注,源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北京一個回顧文革後十年中國大陸文學發展的座談會,因而被稱為中國文壇的「黑馬」。總結八六至八九年間劉的思想,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就「全盤性的反傳統」(或稱「全盤西化」)。2這種主張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其中一個重要思想流派,主張者深信,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之所以如此漫長,關鍵就是傳統文化成為阻礙現代化的重大阻力。
當時劉曉波指出,中國文化由於深受儒家傳統的影響,重視「天人合一」,強調對人性的樂觀(性善論),使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道德人格萬能」,因而形成「人格狂妄」。不過,在「狂妄」的同時,中國人又有極度「奴化」的人格。這種傳統文化深層所模塑的國民性,正是中國不僅不能民主化,反倒在過去產生文化大革命這種瘋狂浩劫的原因。3他反對當代中國的現代化中注入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並指出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一直延續至現在。因此,他呼籲「新中國不應該是傳統中國的繼續,而應該是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現代化中國」。4因此,中國現代化的阻力是傳統,唯有「全盤性反傳統」,方是中國文化的出路所在。「凡是可稱之為傳統的東西就大多是已經形成了的封閉體系,它的惰性必須通過徹底的否定才能打破,而不封閉的傳統只能是反傳統的傳統」,「中國民族的落伍的痛苦現實使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進行徹底的反傳統」。5他的總結是:
「傳統文化的十字架,國人已經背了幾千年,在今日之中國,任何人也無權以任何方式,阻止已經開始覺醒的國人把十字架卸掉。」6
劉曉波這種對中國傳統的全盤性否定,是建基於中西文化的宏觀比較之下的。7換言之,西方文化成為批判及否定中國傳統的參照系。而當他闡釋西方文化的時候,無可避免地便觸及基督教。面對中國歷史的專制主義發展時,劉不禁問:「為甚麼一個在文化上如此重視『個體人格』的民族,卻在現實中野蠻地、殘酷地、隨意地踐踏人的個性和權利?」他不得不得出「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的結論。8劉指出,中國人的問題,就是「不崇拜上帝而崇拜人,把人打扮得如同上帝一樣金光燦爛(從周天子、孔聖到馬克思、毛澤東)」,「崇拜人是人的最可怕的墮落」。「中國人不崇拜任何神,只跪在掌權者的腳下,把權力當作神來崇拜」。9
面對上帝
在批判及卸掉中國傳統的十字架的同時,劉把眼光轉向基督教的上帝及那「血染的十字架」:
「每當我提起筆時,常常想像人與神之間的對造。……當真正的教徒走進教堂,面對血染的十字架時,上帝的注視會使他們以極為虔誠的態度,毫無保留地傾訴內心世界。無論人的靈魂多麼邪惡,但真誠的懺悔是純潔的。在學術上,必須推倒發號施令的『上帝』,但不能沒有一雙『上帝』的眼睛,因為『上帝』的目光容不得半點虛偽。罪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飾罪惡。」10
在劉氏八十年代後期的著作中,「基督教」與「上帝」往往與懺悔的精神連在一起。他指出,中國文化「最致命的謬誤」就是「對謬誤的沒有自覺」。相反,「西方人有絕對的上帝,因而可以懺悔、贖罪;中國人沒有上帝,因而從來不會懺悔、贖罪。」11他曾說:「我相信,懺悔和認罪之時的人是最虔誠、最透明、最富於生命力和激情的」,沒有終極價值(即上帝),悔悟便變得沒有意義。唯有冀求神聖的生命才是真實的。「抬起頭,仰望上蒼;低下頭,捫心自問;做到了這些,人生就會充實,就會神聖,就會期待上帝的降臨」。12
筆者以為,劉曉波這種對基督教及上帝的欣賞,其實只是把基督教及上帝的「超越價值」,作為批判傳統的其中一個「假設」及「參照」。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本身只是某種「絕對的理想」,而針對西方文化本身,基督教及上帝又未嘗不是這種「絕對理想化」的流露。
大夢初醒……
一九八八年八月,劉應邀到挪威講學,十二月再到夏威夷大學訪問。在美期間,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認識與體會。他說:「我對中國之反省所借助的理論武器都是已知的、現成的,無需我的新發現。……當我走進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我才醒悟到我曾經討論過的諸種問題對於高層之(次)的精神創造來說,是多麼的無意義。……我希望自己能夠放棄過去的所有虛名,從零開始,在一片未知的世界中進行嘗試性的探索」。劉承認,他「忽略了或故意迴避了西方文化的種種弱點」,結果變成「向西方文明『獻媚』,以一種誇張的態度來美化西方文明,同時也美化我自身,彷佛西方文化不但是中國的救星,而且是全人類的終極歸宿。」他更進一步作自我反省:「而我借助於這種虛幻的理想主義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事實上,西方文化自身仍面對許多危機,甚至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也變得日益世俗化,「人類親手殺死了自己心中的神聖價值」。13
這種體認,令劉感受到「手足無措,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之中」。他說:「我猛烈醒悟:我是在用已經陳舊的武器去批判另一種更為陳舊的文化,以一個半殘廢的自豪去嘲笑一個全癱的人」。「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對真實的生命呈現和殘酷的人生抉擇。當一個人從虛幻的高峰一下子墜入真實的深淵,才發現自己始終沒有登上過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淵中掙扎。這種大夢初醒之後無路可走的絕望,曾使我猶豫、動搖,並怯懦地嚮往那個我瞭如指掌的土地」。14
再走上十字架到走下十字架
沒多久,在劉曉波熟悉的土地上,一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正在北京揭幕。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劉登上紐約的航班回國,並逐步投入學生運動。他的「救世主」心態再次被挑動起來,「肩及重任的使命感和赴湯蹈火的英雄感便油然而生」,「英雄夢便纏糾著我」。15他在六月二日與另外三位知識分子發起絕食時,他把自己視作十架上的殉難者:
「我忽然感受到這世界上最美的傑作就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人類的苦難由他一肩擔起,他代表人類受到上帝的懲罰。但他的受難不是屈辱,而是榮耀;不是失敗,而是成功。……面對殉難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氣走上去。毫無懼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聖人,退怯者即庸人。絕食也許會成為一次殉難,而且是千載難逢的殉難時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不做殉難者誰做!」16
劉曉波在「十字架」上只「釘」了兩天,便發生「六四」。6月6日,劉被中國政府逮捕,到1991年1月26日因其「悔罪」而獲釋。劉事後對自己「悔罪」一事表達了強烈的懺悔。於是帶著「懺悔」的心深入反省及剖析自己在六四前後的心路歷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再次想起「上帝」:
「……十全十美的上帝卻創造出罪惡纍纍的人類,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在心理上彌合這一裂痕的辨法只能是懺悔。完美的上帝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筒,懺悔就是清潔工。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完美,更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容忍罪惡。只有上帝才能超然於人類之上,以寬容的態度無限制地接受人類的一切罪惡。……
「如果這世界沒有上帝,人類也會變得聖潔,既不作惡也不懺悔。但這僅僅是『如果』。沒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無意義,上帝就是為人的罪惡而存在的。
「那麼,人類只能在兩種現實中進行選擇:要嘛是有上帝、有罪惡,也有懺悔的世界;要嘛是只有罪惡而沒有上帝,也沒有懺悔的世界。
「我選擇前者,故而寫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7
自始至終,在劉曉波的心中,「十字架」均具濃厚的象徵意義。他早期所體認的十字架及上帝,反映出其主要關心的,是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毋庸置疑,這位「黑馬」內心深處,仍深深烙下「救世主」的心態與印記。這種心態,在六四期間成為劉氏思想及行動背後的重要推動力。六四後,他深切地挖入自己的內心,坦誠面對自己。這時他所體認的十字架及上帝,已成為一種自我批判的參照。劉曉波不再是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及「殉難者」,卻成為一位誠實面對自我的懺悔者。
作者聯同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程翔先生,將於十二月八日晚
於宣道會北角堂主講公開講座「和平.崛起──由諾貝爾和平獎到劉曉波的信仰視域」
- 1.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台北:時報出版社,一九九二),頁54。
- 2. 有關劉氏的反傳統主義,參顧昕:《中國反傳統主義的貧困──劉曉波與偶像破壞的烏托邦》(台北:風雲時代,一九九三)。
- 3. 劉曉波對天人合一的批判,參氏著:《選擇的批判》(台北:風雲時代,一九八九),頁183至234。本書原於一九八七年1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社。)
- 4. 劉曉波:〈「五四」運動反思〉,《蛇口通訊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廿六日。
- 5. 劉曉波:《選擇的批判》,頁4至5。
- 6. 劉曉波:《選擇的批判》,頁234。
- 7. 他早期便致力於中西文化的對比,參劉曉波:〈衝突與和諧──中西審美意識的根本差異〉,《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一九八六年四期,頁11至19;〈再現與表現──中西審美意識的比較研究〉,鍾敬文編:《東西文化研究》,創刊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頁107至127。
- 8. 劉曉波:〈狂妄必遭天責──論中國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謬誤〉,氏著:《悲劇.審美.自由》(台北:風雲時代,一九八九),頁74。
- 9. 劉曉波:〈形而上學與中國文化〉,王元化編:《新啟蒙(一):時代的選擇》(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頁64、66至67。
- 10. 劉曉波:《選擇的批判》,頁236。
- 11. 劉曉波:〈狂妄必遭天責──論中國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謬誤〉,頁67。
- 12. 劉曉波:〈狂妄必遭天責──論中國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謬誤〉,頁74。
- 13. 劉曉波:《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台北:唐山出版社,一九九○),頁158至161。
- 14. 劉曉波:《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頁161至162。
- 15.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頁71、80。
- 16.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頁190。
- 17.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頁9至10。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基督教歷史、香港基督教歷史及當代中國政教關係。近著有《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