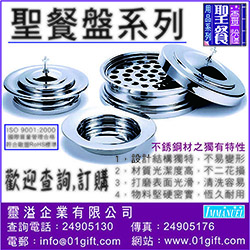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
| 何光滬教授,中國著名宗教哲學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以及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近著包括《神聖的根》、《月映萬川──宗教、社會與人生》、《天人之際》、《百川歸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學》、《信仰之問》等。。 |
第二代學者是一九八○年代初期三十歲左右,也就是現在五十歲至六十歲左右的一代人。他們在世界觀形成的時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幻滅,所以不像上一代學者那樣牢固地確立了官方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們更為靈活、開放,也更瞭解中國社會的實際(因為他們多半都有「上山下鄉」或在基層生活的經歷)。其中一些人在「文化革命」時期的封閉之後,終於可以接觸外部世界之時,發現有一種博大精深的西方傳統,即基督宗教至少是值得瞭解的。於是,他們經歷了我所謂「從了解到理解」的過程,其中一些人更投入了時間精力進行研究,促成了基督教研究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這些學者中又有少數,在尋求自我或個人的精神出路,或在尋求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出路之時,在基督宗教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穫,或者甚至以基督宗教作為出路,從而皈依了基督教。
這第二代學者的研究,較多地涉及到神學,特別是西方神學的介紹或研究,但除了少數的例外(主要是其中居於少數的基督徒學者),還不算了嚴格意義上的神學,換言之,還只是站在神學外邊看神學。但在當代中國的學術環境下,這依然構成了神學得以發展的重要條件。正是在這一代學者比上一代學者更多的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所謂「狹義的漢語神學」運動從一九九○年中期以後才得以發展起來,從而不僅大大繪了當代中國的基督宗教研究,也大大推動了真正的基督教神學在衰亡多年之後的復甦。
3.3中國神學的演變、發展與教會處境
第三代學者基本上現在是五十歲以下,即一九六○年代以後出生。他們受到革命狂熱和「文革」動亂時期的影響較少,也不像第二代學者那樣被迫停止了中學和大學的學業。所以他們所受教育較量為系統,同時,因為生活在革命意識形態已喪失「公信力」的時期,並不像第一代學者那樣篤信學校裡教的那一套馬列教條。他們較多的基督教資料(包括第二代學者的不少翻譯),其中一些還有機會到國外留學。所以,我把他們的學術經歷歸結為「從學習到專精」,就是說,較好的學習條件已使得他們的基督教研究可以在總體上比前兩代學者更為專業更為精到,這其中就包括更多的神學研究。
這一代學者可以做更多的更地道的神學研究,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當中更多的人經歷了對基督教「從興趣到委身」的過程,換言之,他們當中有更多的人變成了基督徒。這當然也是一九八○年代以後基督教在中國迅速復甦並奇蹟般地生長的結果。
這一代學者不但在人數上大大超越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學者,而且其研究領域已不像前兩代學者那樣局限於「基督教研究」(Christian Studies),這就使得中國神學有可能回到自身並有所發展。正因為如此,我稱之為中國神學的演變與發展。
這一重大變化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國教會的發展,尤其是城市家庭教會的發展。
眾所周知,從廿一世紀開始,中國家庭教會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尤為明顯。這發展的一大特徵,就是教會成員的教育程度有了飛躍式的提高──儘管成員多為半盲半文的農村家庭教會,依然是中國教會的主體,但是有不少海外留學歸來者和中國名校畢業者加入或領導的中心城市新興教會,卻擁有大量大學生和專業人士。這種情況與部份大學教師和學者的基督教研究相結合,就造成了中國神學演變和發展的契機與條件。由此,我們不但可以看到部份「以書代刊」的出版物上1有了明顯增多的神學論文,而且可以看到大量碩士和博士論文以神學研究課題作為主題,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教會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並在上面刊登神學文章。
儘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國,除了三自教會不能公開發行的《金陵神學志》和天主教愛國會不能公開發行的《神學研究》之外,依然沒有一個專門從事神學的公開雜誌,也沒有任何神學家的聯合協會之類組織或神學專業的學術會議,前述家庭教會的雜誌不能公開發行,三自教會、家庭教會和大學及研究構成內的神學工作者也基本上各自為政互不溝通。
所有這些,當然也是中國當今教會處境的必然結果。這種處境的最大特點,就是三自教會受到黨和政府的嚴格管制,而家庭教會則長期處於非合法地位,無法辦公開活動,很難進入公共領域。同時,由於中國的大學和學術機構基本上都是國營的或由國家控制的,而國家的政策一直是嚴格提防任何基督教的因素發展大學和學術機構,所以在大學和學術構成中,神學也沒有合法或公開的地位。所有這些,注定了神學在今日中國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不但必須面對困難而繼續工作,而且必須仰望蒼天保持希望。
四、結語:中國神學的特徵與趨勢
4.1回顧:從政治到社會到教會
回顧既往從西元七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一千三百年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神學的一大特徵,就是其關注的重心是從政治到社會文化,再從社會文化到教會。
唐朝景教文獻的內容,顯示出景教關注的重心是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元朝也裡可溫教神學文獻的缺失,顯示出也裡可溫教關注的重心是對政治結構的適應。明末清初中國神學的誕生,本身就是天主教傳教士適應中國社會文化的結果,而此後近一百年的中國禮儀之爭,本身也是在對應社會文化方面的鬥爭,這些都反映出中國神學不得不高度關注中國的社會文化問題。清廷禁教和新教傳入之後發生起來的中國神學,從梁發批判佛道和民間迷信,到吳雷川等尋求儒家與基督教的共同點,從重視聖經漢譯(和介紹西學),到重視社會福音(和社會革命),全部都顯示出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不得不高度關注中國的社會形勢和社會文化問題,而這當然會在中國神學中留下明顯的痕蹟。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後期(一九三○到一九四○年代),由於中國社會的開放和中國教會的發展比較正常,一部份中國教會領袖如王明道和倪柝聲等人開始把關注重心轉向信徒的「靈命」培養和教會的「屬靈」使命,而且在這個方面留下了一筆可觀的遺產。這可以視為中國神學在整體上終於「走向教會」的明顯表現,只不過,這些表現維持的時間不長,就被一九四九年開始的由政治造成的社會衰落和教會衰落所淹沒了。
4.2展望:從教會到社會到政治
站在廿一世紀起初十年的位置展望未來,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種同以往一千三百年完全相反的趨勢,即中國神學將不得不把關注的重心裡從教會轉向社會文化,再轉向政治。
儘管如上所述,以個人靈命和教會使命為重心的中國神學壽命不長,是這一特徵或這種重心卻一直存在於中國教會甚至海外華人教會之中。而且,這種情況也已反映在中國家庭教會剛開始出現的神學思考或出版物之中──在當今的中國大陸教會處境下,他們也不得不把思考和言論局限於較少政治敏感和較少公共性的話題上。
但是,這種以教會為重心的神學言說已開始顯現出部份的改變,即開始關注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與其基督教的關係,包括儒家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同基督教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由於當代大陸新儒家十分關注基督教,或者同政府一樣關注提防基督教的「文化滲透」。無論如何,這一點,再加上中國當代社會矛盾和文化危機已到了任何人也不能迴避的程度,必然使得中國神學不能不關注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新的趨勢也已經初露端倪,那就是對社會政治或政教關係或政治理論的關注。2從總體上說,這並不是中國教會主動的或有意識的傾向,而是教會所處環境的驅使所至。由於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的處境,最大的問題來自政教關係和政治結構,儘管絕大多數教會領袖不得不刻意回避這類問題以求自保,但是由少數學者或神學工作者開始思考、寫作而引起更多的關注和思考,肯定是一個無法避免的趨勢。
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觀察結論。但我相信這個趨勢是必然的,我還相信這個趨勢是有益的,不論是對神學本身,還是對教會、對社會,都如此。
編按:原文約一萬二千字,分兩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