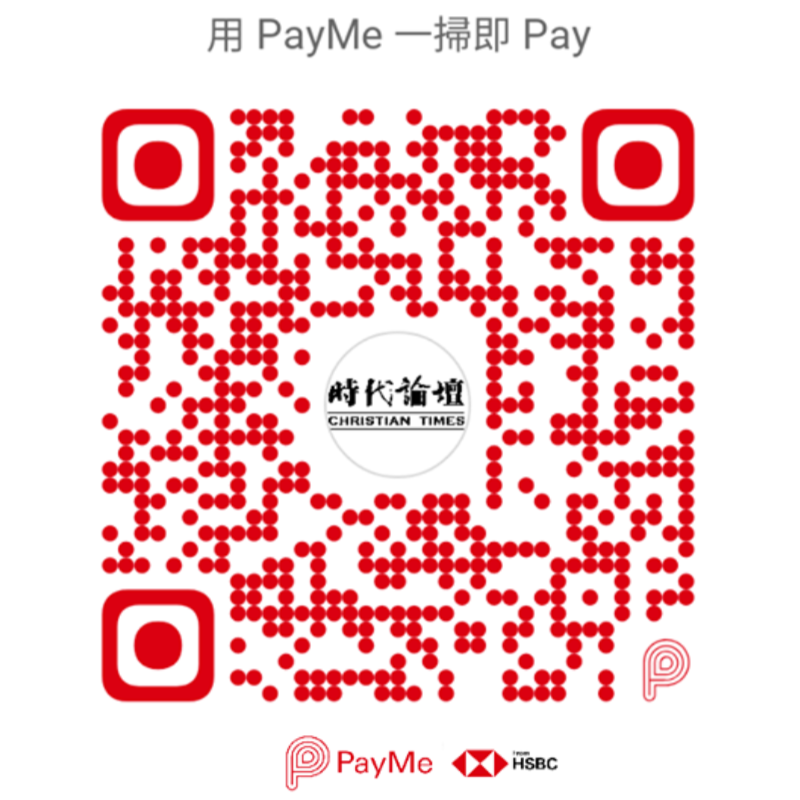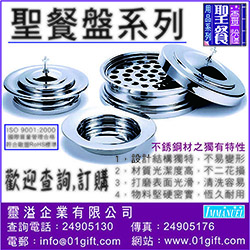蔡子強在七月十日《明報》發表〈無力正乾坤〉一文,道出作為溫和派的無力感,特別屢次嘗試從中間派角度出發,貢獻香港民主運動的知識份子,他飽受指摘下仍筆耕疾呼,他自然更感無奈。面對無恥的特首、有強權無公理的議會及助紂為虐的警隊,蔡子強慨歎:「我還可以再說些甚麼?」他的無力感同樣見諸於不少人身上,而他所擔心的不獨是個人憂慮,更反映某種社會現況,就是「公民社會與政府開戰,已經瀕臨一觸即發」。最後,蔡子強忍不住反問按此情勢發展下去,他仍能當溫和派多久。看來劇本已被寫下、角色已然分派,那麼故事的結局如何?從文中端倪看出其測度,悲劇命運似乎不可避免。
強大的暴虐政權、叫囂的狐朋狗黨、吶喊的群體烘托出故事主角正步上受苦道路,二千多年前是為人的罪付上生命的耶穌基督,今天是為民主普選付上代價的新生代。社會制造的集體暴力,就是為了平息危機,由一個人或一小部份人成為代罪羔羊,殺害他/他們,以換來社群的穩定。或許,悲劇命運未成定案,但從香港及中央政府種種舉止,我們能抱持樂觀的態度嗎?或許,這正導致致命的無力感及背城借一的心態。命運(fate),看似封閉的世界,我們各按劇本演活角色──施暴者、受壓迫者/受苦者及圍繞的群眾。筆者十分欣賞蔡子強的分析,但在世界政權中尋求good faith,注定痴心妄想、緣木求魚。從基督信仰來看,只有受託見證上主國度的教會明辨世界命途,故能打破此悲劇故事。問題是信仰群體會否迷失在世界的遊戲規則、抗爭行動中,結果乏善足陳。
部份信徒認為「佔中」是回應今日香港處境的最後一張王牌,並視之為持有「終極武器」的抗爭行動,但這選擇正反映出言說者受當下情境限制:「這情況下我有甚麼選擇?」或「這情況需採取甚麼行動?」即我們被處身的環境塑造自身的回應/抗爭行動,但若信仰群體根植於上帝本性,那我們的回應便應超越處境所給予的條件、選擇、機會及模式,因此尤達(John Howard Yoder)認為更恰當的提問是:「聖靈賜下生命的力量,如何超越現有模式及選擇去完成新事,而這新事將見證上主的臨在?」1當信徒聲稱今日別無選擇,只有投身此終極一戰時,其實是接受了一個前提:社會制度的操作是決定性(deterministic)或機械性(mechanistic)的。2事實上,這假設只有一種被程式化的抗爭方式,故此要逆轉香港困局的唯一方法,便要如劉兆佳所觀察那樣,作出「競爭性動員」,因為只有輸入更強大的力量才能壓倒對方, 3故此擁有龐大人數的團體,自然成為爭取招安投誠的單位,這包括公務員隊伍、警察及教會等,亦因此近日社會出現不少低水平的「反佔中」行動。無論教會以甚麼理由被收編參與正、反的抗爭隊伍,只要仍為當下情境塑造其回應模式,事實便接受了上述假設,最終不自覺地否定自身作為上主施事者(agency)的角色,同時否定處境中其他行動者的位格性。4
對支持或反對建制的基督徒來說,他們的抗爭行動都只承認存在於系統內的盼望,而忘掉超越系統或在系統之上的盼望。5耶穌基督實現了應許:藉其復活及升天(ascension)回應命運──悲劇世界裡的命運,以打破這封閉世界裡的罪惡循環。同時接續耶穌升天的敘述是耶路撒冷教會被建立,門徒被招聚過來,目的是見證一事,就是於強暴的命運下仍有新的可能──復和及建立團契關係。這是教會被召的使命:「轉化命運為天命」(transforming fate into destiny),因此,教會的「抗爭行動」本性上與「佔中」抗爭不同,信徒聲稱「佔中」是最後一張王牌時,其實是接受在這封閉的世界裡,按照命運既定的劇本演活當中的角色──施暴者、受壓迫者或群眾,但聖經卻見證教會在聖靈指引和加力下打開新的世界,6於是教會的「抗爭行動」不是拒絕(blocking)或接受(accepting)處境,而是「超乎地接受」(overaccepting)。與此同時,教會的他性(otherness)正道出不少支持者「佔中」者的謬誤。呂大樂曾指好些激動分子期望「佔中」是跟北京的終極決戰,這將「佔中」轉變為他們心目中的那場「政治沙蟹」,即在中環上演一場決鬥。(《明報》觀點,七月四日)當然他們為了追求公義,不惜承擔政治風險,為普選付上代價去爭取民主政制的意圖是值得肯定(如七月二日的預演「佔中」),但信徒有否另類的「抗爭行動」呢?
從聖經敘述所見,耶穌並沒有被動地成為交付罪價的受害者,反之祂主動地在傳道生活中反對具體的罪惡、不公和壓迫,這見於耶穌與反對者、當權者針鋒相對的故事──撒馬利亞人、面對行淫婦人、安息日治病及潔淨聖殿等。7這展示出耶穌不斷藉生活的經歷去挑戰更根本的牢宰──邪惡權勢的捆綁,這不獨見於耶路撒冷,同時見於生活上不同層面。於是耶穌挑戰不義的方法,並非被動地在某地受害,而是主動地在那三年的傳道生活中挑戰邪惡權勢,並且邀請被壓迫者和受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一同確認上帝的統治、更新彼此的生命、一起對抗藉不同方式奴役他們的壓迫處境,而上主的恩典則是讓我們參與耶穌那方,8故此耶穌基督的「非暴力」行動,並非獨見於耶路撒冷內,因為抵抗邪惡的場景是生活、解放的對象包括被壓迫人民和壓迫者。9「佔中」倡議者強調要攻向香港最脆弱的地方,以令北京政府和特區政府如不落實真普選的承諾,就得付出沉重的代價,而預演「佔中」看來亦分享同樣策略,於是「佔中」成為被壓迫者反抗壓迫的手段。可是耶穌在世的工作,卻明顯打破這分類。耶穌的工作挑戰壓迫者意會到自己是壓迫的同謀者,於是開始採取行動,以消除壓迫,與此同時,祂同樣挑戰被壓迫者,因為他們可以參與加在自身的壓迫,即讓壓迫性的結構來定義人的實在。10 於是耶穌的教導及生活是展示「生活之道」(the way of life),而人們通過這些踐行見到上帝的統治如何挑戰世界,由此而言,耶穌的生命和教導是上帝管治的見證,也是另類的抗爭行動。11進一步理解當中的基礎,便離不開有關「權勢」(Powers)的討論。
伯克霍夫(Hendrik Berkhof)在《基督與權勢》(Christ and the Powers)12裡分析保羅書信中九段有關「權勢」的經文,從而指出保羅並沒有設想權勢有任何位格化的意義。權勢似乎是其中影響和控制地上的創造實在(created realities)。按伯克霍夫分析,保羅似乎把「權勢」置於管轄宇宙的結構來思考,甚至連上構成及規管人類道德事務的東西,諸如傳統、法規、規章和道德學說等(西二)。問題是權勢已然墜落,不再在基督裡聯繫上主和受造世界。事實上,權勢表現出它們成為存有的最終依據,並成為眾神(gods)(加四8),要求人作出崇拜。簡言之,墜落權勢的滲透性令受造物放大自身的位置。權勢把上帝與人分開,並站在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間成為障礙。伯克霍夫認為,教會的存在便是蔑視和反抗權勢的行為,因為當人認信耶穌為主時,便在權勢面前作出抵抗。抵禦權勢意味著教會自身的生命要表現出合乎耶穌基督示範的生活之道,以對抗時代的眾神。教會的生活要拒絕瑪門、種族主義、不公義、歧視和壓迫的權勢,因為這些權勢將引誘教會敬拜新的神祇,而否認耶穌基督是主。當教會在權勢面前承認耶穌的主權時,並不意味要推翻和消滅權勢,相反是要創造一個地方去質疑權勢的合法性,並在耶穌的主權下展示出全新的社群、道德、政治和經濟關係模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教會便動搖權勢的位置,這同樣構成教會的另類抗爭行動。基於權勢的滲透性,於是只有通過生活之道去挑戰它們。這無疑會引致受苦及死亡,但如韋弗(Denny J. Weaver)所言,受苦不是救贖和其自身,它不是上帝的目的,因為上帝並非藉此引人注目,受苦只是反對邪惡的副產品,耶穌並非期望被人虐打,祂的受苦和死亡是因為祂示範生活之道去反對邪惡權勢的結果。13
故此,耶穌並非如支持「佔中」者所指那樣,成為順服被虐的典範,救主的典範是積極地在日常生活中主動對抗拒罪惡和壓迫。14或許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非暴力只要淪為手段,或許可以成為暴力的工具。」因為人可以在沒有行使暴力下去鄙視、恨惡、侵佔和壓迫他人,這豈不見於特首及吳亮星的行動。於是尤達認為「非暴力」的意思已被混淆,指「不抵抗」比「非暴力」更有力和精確,即要軟弱地接受那惡者的意圖,順從他邪惡目標,而不是在他的設計中同謀,這意味更要關懷那些執意行惡的人,15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參與「佔中」者的人鏈策略,是否恰當地反映「不抵抗」的精神?當警方清場時,參與者自行上車,這將帶來甚麼的情況?在強大的武裝設備下,參與者只默默跟從,那世人觀看到是甚麼景象?
為甚麼「佔中」並非對抗不義的終極手段?因為罪惡不獨出現在中環、遮打花園,它背後的權勢滲入不同社會層面,它製造恐懼及謊言,在群體內、外蔓延白色恐怖,而《主場新聞》結業豈不見證此事?我們用主動的行動,引來蓄意的受苦對抗,其實可能美化受苦,且作為工具,引來對方施行暴力。我們未必為感召敵人,但郤是為醜化、惡魔化他們,這骨子裡豈不同樣是以暴易暴?但這正是那惡者的誘惑,因為耶穌是從與撒馬利亞人、面對行淫婦人、安息日治病、潔淨聖殿下對抗不公,祂挑戰整個受權勢滲透的生活結構,在其中祂要帶來生命,而非受苦,祂要釋放受苦者,而非帶來不幸。故此,這不是尋找受苦英雄的日子,而是尋找中止悲劇資源的時候,香港教會不能制造英雄,但能遏止悲劇。就讓教會根植本源,重拾我們更徹底的革命工作,回歸日常生活裡的抗爭,這豈不就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無權力者的權力》提及要「在真實中生活」,即做一個說真話的人之意。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7.29)
- John Howard Yoder, The Original Revolution: Essays on Christian Pacifism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2012), 49.
- John Howard Yoder, “The Church and Change: Violence and its alternatives,” The written paper of a presentation given at the 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 July 24, 1978, 14.
- Yoder, “The Church and Change,” 14.
- Yoder, “The Church and Change,” 14.
- Yoder, “The Church and Change,” 14.
- Yoder, “The Church and Change,” 15.
- Denny J.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2th ed.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2011), 318.
-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318.
-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319.
-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318.
-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319.
- Berkhof Hendrik. Christ and Powers. Translated by John H. Yoder.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77.
-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319.
- Weaver, The Nonviolent Atonement, 318.
- Yoder, The Original Revolution,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