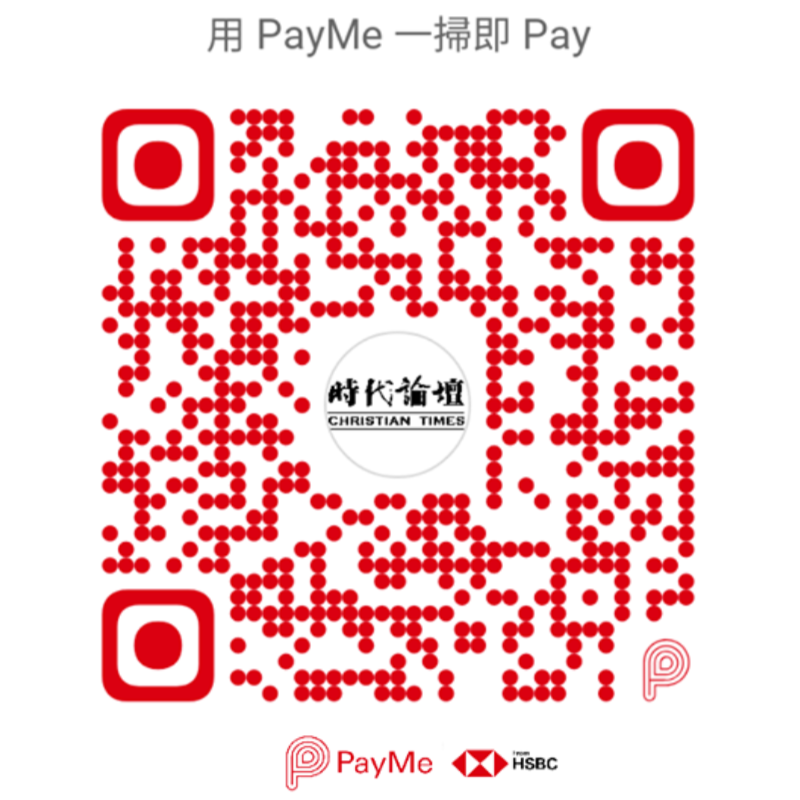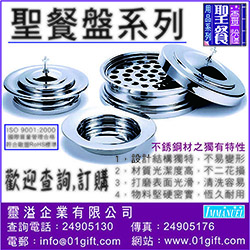一代佈道家葛培理牧師逝世,有人慨歎福音派中再找不到像他這樣的一位領袖。在這時代中,我們需要另一個葛培理?如何理解葛培理與他的時代,以至思考福音派教會在今日世界中該走的路?
葛培理:一個時代的開創與終結
•呂慶雄
被視為上世紀最偉大的佈道家葛培理,他的離去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正式終結。葛培理在基督教發展歷史上肯定佔有一席位,但歷史不會再有第二個葛培理。
我曾參與兩次葛培理佈道大會,第一次我還是小學生,跟兄姊到了大球場。現在回想起來,不知是甚麼原因,當時情景還歷歷在目,我沒有走上前決志,但還記得即時傳譯的是謝志偉博士。他宣講的信息簡單易明,我還記得他引用了約翰福音三章16節來呼召。第二次,我已在謝志偉任校長的大學讀書,我也成為佈道會義工,當時的即時傳譯是陳恩明牧師。約十年前,他的兒子葛福臨來港,我所屬的機構有份協助籌備,但我人已在美國進修,無緣進一步參與這大型佈道事工。
葛培理可算是一個時代的開創者。曾出現在他主講的大型佈道會的參加者數目,紀錄應該不會被打破。善用科技傳福音與牧養教導,他是表表者,是最早期使用電台與電視進行佈道與聖經教導的先行者之一。他並不離地,神學光譜也闊。他與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同行支持黑人民權運動,同時又出任多位美國總統的顧問。與曾被評為成功神學代表牧者蕭律柏(Robert H. Schuller)為至交好友,又與福音派翹楚斯托得(John R. W. Stott)聯手推動世界宣教運動,在七十年代開始洛桑世界宣教大會,直接影響了世界華福中心的出現。
他的確開創了一個時代,一個善用多媒體,又以大型佈道會為主體的福音運動。今日仍然善用多媒體,然而這些媒體較前更為個人化,畢竟,我們這個時代變了。不要大(macro)、只要小(micro);少談普世、多講本土。以前講大異象與偉大夢想,可以震撼人心,台下掌聲與淚水交雜。今日多由自我實現出發,為神而活的前提,是活出真我。選擇佈道會?不如多善用關係佈道。同時,隨著超大型教會的興起,有一段時間堂會運作成功之道成為大型聚會的主要內容,而不是佈道會。名人效應(葛培理)與福音機構(佈道團)再難以號召群雄。
劃時代的影響力,會因著時代與環境因素,配合個人特質而產生。葛培理留下不少屬靈遺產,他雖不完美,但卻屬於少數在事奉生涯上可以「善終」(finishing well)的屬靈人。我們今日不要妄求另一個葛培理,更不要拿那一代的前輩來比較今日的教會領袖,那時代已經結束。與其緬懷昔日,不如求主賜下這時代的信息。也許,神今日不用人做大事,只做小事,又透過這些小事編織神國的真正大事。
洛桑福音運動的唯一始創人:葛培理牧師
•關浩然
提起洛桑福音運動,最多人想起的人物無疑是約翰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因他是《洛桑信約》的主要撰寫人,也是其思想旗手。一九七五年洛桑會議出版的《洛桑信約》註釋亦由斯托得親自撰寫。但洛桑運動的網頁提到其始創人(founder)時,只列出葛培理牧師一人。
葛培理是最為世人認識的佈道家,曾於一九五六、一九七五、一九九○年來港主持佈道會,帶動了九十年代以降香港本地大型聯合佈道聚會的風氣。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我認為是發起及繼續支持一個跟他自己的想法有距離的福音運動。
葛培理佈道團受邀請到世界各地佈道,因此他結識了各地的福音派教會領袖,但卻發現人們彼此不認識,於是有感要把眾人連結一起。這催生了一九六六年在柏林的福音會議及其後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洛桑會議由葛培理負責開幕演講(演講辭可參此網站),並制訂了《洛桑信約》,建立起一個普世福音派領袖合作的平台。
斯托得與葛培理是親密的戰友,早於一九五五年已在劍橋大學的學生團契一同作工。(根據Alister Chapman的研究,斯托得是透過葛培理的引介,得以在英美和歐洲的福音派教會中漸漸建立影響力,葛培理是“the senior partner”。見Godly Ambition. OUP, 2012. p.50.)《洛桑信約》的主調是傳福音與社會關懷都是教會必須的任務,它的第十三段是關於自由和逼迫,其中甚至提到教會要呼籲政權履行《國際人權宣言》對思想與良心自由的保障,關注那些不公正地被囚禁的人。這信約沒有叫教會成為政治動員組織,但教會關注政治迫害的角色是十分明顯的。總體上,《洛桑信約》把從前只在所謂「社會福音」中有的關注,重新帶回福音派的「向世界傳福音」的任務中,是當時的突破。這是斯托得的福音遠象。
葛培理本人對傳福音任務的看法與《洛桑信約》有點距離。在洛桑運動的網頁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斯托得牧師對洛桑運動有形塑性的影響(formative influence),其中一段提到在一九七四年大會之後,一九七五年在墨西哥召開的接續工作會議上,有相當多人屬意由葛培理作洛桑運動的主席,但斯托得反對,也提出如果要由葛培理作主席,就必須同時設有多位副主席。最後該工作會議由斯托得起草報告,經輕微修訂後獲接納。
Alister Chapman在斯托得牧師的傳記Godly Ambition中解釋這事。原來曾經在洛桑會議中批評教會忽視社會關懷的兩位主要人物並沒有被邀請參與這工作會議,並且這工作會議的初稿只集中在傳福音,而沒有持守《洛桑信約》的突破: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並重。斯托得知道自己是這會議裡的少數派。在會議的首晚,葛培理說「我建議我們嚴格局限(stick strictly to)在傳福音和宣教,同時鼓勵別人去作神指示教會去做的專門的事。」《洛桑信約》努力撮合的,葛培理倡議分家。斯托得翌日表示假如執行葛培理的方向,他會辭去這委員會的職務。斯托得重申洛桑運動產生的組織必須持守《洛桑信約》的雙軌精神。
作為洛桑會議的主要資金供應者,也是國際上最知名的佈道家,葛培理牧師並沒有強推自己提出的,也是當時會議上較多人支持的「分家方案」。其實葛培理當時絕對有本錢這樣做。(Godly Ambition, 137-143.)斯托得一直是洛桑運動的思想領袖,而葛培理也一直在洛桑運動上押上自己的名字。兩位巨擘的路線分歧一直存在。斯托得一九八四年出版《當代基督教與社會》(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一書,落實他的遠象。而葛培理解釋他不參加八十年代美國右派的「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的原因,是因為他要站在中立之地,才能向所有人傳福音,包括思想左傾的和右傾的(注意此乃市場原因而不是神學批判)。(葛培理牧師能否如他所想的在政治上站於中間,則是另一回事。)雖然分歧存在,葛培理卻依然一直支持洛桑運動,二○一○年在南非開普敦召開的第三屆洛桑會議,照樣得到他的祝福。
告別大量生產、複製的基督教
•戴偲馨
若說葛培理帶動了一個時代,他的離去又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那他帶來和帶走的,又是甚麼?
大型佈道會當然非葛培理所創。早期的他,承傳著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期幾位美國佈道家的路線,乘著當時美國國內的社會政經處境而發揚光大。他開始全職以佈道為業的時候,正值大戰結束,美國人的心靈和經濟都百廢待舉,大眾傳媒高速發展,政府為重建經濟而大舉刺激消費,工業進入了空前的大量生產和商品劃一(standardisation)的時期,美國的工業和文化產物也大規模出口到世界各地。葛培理和他的團隊,就此乘時而起。
只能說,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son of his time)。他跟團隊採納了大規模工業生產的模式,把佈道會的程序、信息、跟進方式以及各樣配套,全部劃一,確保效率和質素,又適時使用不斷發展的傳播科技(電台、電視、人造衛星),把基本上相同的信息,發送給未能親赴現場參與的人。
香港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經有趙世光、計志文等租用大型戲院開佈道會,決志者數以千計。但是一九七五年葛培理一來,以其個人魅力和能耐,拉得不同宗派落水合作(衷誠與否是另一回事),連續一週租用有二萬八千座位(未計草地)的大球場,又接通隔鄰一萬多座位的南華會球場作轉播,招募千人詩班,用製作精美的劃一材料培訓陪談員,連續數週在電視黃金時間賣廣告宣傳,攝製現場紀錄片日後多次播放。對於當時還在山寨時期的一般香港教會,這些舉措怎不令人瞠目結舌?
就是這樣,這套講求大量、劃一、包裝、緊扣傳播科技的美式基督教佈道策略,透過葛培理出口來到香港(以及無數其他地區),從此也讓香港基督教的氣質變得比以前更加貼近美式福音派——我必須強調,是「美式福音派」,而非總體上普遍的、普世的「福音信仰」;兩者差異微妙卻顯著,非本文所能闡釋。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也即是七五年葛培理來港之後),世界開始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商品消費市場講求分眾化、個人化而抗拒劃一量產;平凡百姓生活高舉本地意識和地方文化傳統,不喜歡缺乏本地特色的外來文化,更抗拒大財團大帝國的霸權;基督教神學和信仰表述也愈來愈重視本土處境經驗,對放諸四海的單一信息感到懷疑。
如是,葛培理和他所屬於的那個時代其實早已過去了。我們可以緬懷,可以研究,可以反省,可是如果硬要仿效那個時代的做法,那恐怕是時空錯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