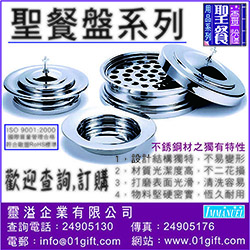進圖兄自二○一七年九月開始,每週都會撰寫一封信給因東北發展案、公民廣場案及佔旺藐視案而被牢的青年人。如此持續的工夫,需要的不僅是恆心與毅力,更重要的,是一種對言說的堅持與熱誠。
敢問:在這個強權當道,謊言充斥的世代,言說仍有作用嗎?我想起耶穌跟門徒說的一段話:「我該用甚麼來比這世代呢?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們為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唱哀歌,你們不捶胸。』」(太十一16-17)面對冷漠(indifferent)的世代,言說是否只是自說自話?
其實,沉重的無能感,甚至也出現在言說者身上。目睹理想及價值的崩壞,甚至連自己曾持守的信念,也有動搖的可能。正如在監獄中的施洗約翰派人來問耶穌:「將要來的那位就是你嗎?還是我們要等候另一位呢?」(太十一3)新約聖經中的施洗約翰,被視為耶穌基督開路的先鋒。「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路三4)是他一生的使命所在。被牢者約翰的問題,雖不能反映他對耶穌身份的否定,但也表現出其懷疑及不確定。在迷失的當下,很容易有所動搖,這真是我要走的路嗎?如果連自己的信念也不敢肯定是否真的能實現,那麼,又可以言說甚麼?
我相信,進圖兄寫《給下獄青年的信》,一方面是出於那份知其不可為而為知的信念,要藉著書信向這個世代言說。另方面,他的言說,並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答案擁有者自居,卻是讓我們看見,一位基督徒新聞工作者,如何在遭遇兇徒施襲的人生巨變中,「迎鋒而立」,再次在信仰世界中,認定這個世代需要信念及持守價值。他的言說,既是與下獄青年的坦誠對話,也者未嘗不是進入自己心靈世界之中,與自己、這個世界及上主對話。
記得有一次跟進圖兄見面,他分享自己近日在閱讀的書籍。從《給下獄青年的信》中,可見他曾引用的作家及著作甚多,包括: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及《團契生活》;莫特曼的《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被釘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The Spirit of Life、Ethics of Hope;德蘭修女的《來作我的光》;依路(Jacques Ellul)的Propaganda,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魯益斯的A Grief Observed;Jonathan Sacks的A Letter in the Scroll;還有約翰衛斯理、古倫神父、馬丁路德金、盧雲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與迪爾神父(Father John Dear, S. J.),及管理學大師Jim Collins等。不少聖經人物,如約拿、約瑟、約伯、大衛、所羅門、以斯帖等,也曾在信中出現。我相信,進圖兄引述這些著作或內容,是因為當他帶著自己經歷的問題與掙扎來閱讀時,得以與作者的生命相遇。他也期望下獄青年,也能透過閱讀這一扇窗,得以窺探牢室以外遼闊的天空,人在獄中,但心靈及思想卻不被牢禁。
誠如多次被國家牢禁的劉曉波,在〈在刀鋒上行走──獄中讀《布拉格精神》(1999)一文曾說: 「生活在極權制度壓抑下的反抗者,儘管他的聲音封殺,他的身體被囚禁,但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他的筆從未失語過,他的生活從未失去方向。」這正這個世代需要持守,並且言說的信念。
其實,當我在讀進圖兄的書信時,也感覺到他是寫給我的。無疑,我們並非身陷囹圄,但近年社會沉鬱的氛圍,也令人有一種被囚的感覺。記得劉曉波曾說:
我不是走出了小監獄(秦城)而又進入了大監獄(專制社會),而是一直沒有走出自我設置的心靈牢房,不敢面對真實的心靈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謊言的惡性循環的終極根源。擴而言之,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心靈牢房構成了專制社會的大牢房。因而,衝破專制主義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們自己的心獄。
是的,我們並未被囚於那狹小的牢室空間(小監獄),卻是活於強權專制的社會(大監獄),還有自己內心的「心靈牢房」。
這樣看來,《給下獄青年的信》,不僅是寫給廁身小監獄的青年人,也是寫給每一個被困在「大監獄」及「心靈牢房」中的你與我。進圖兄相信,即或如此,這個世代,仍需要言說。言說我們對理想的在乎,對真實的堅持,對記憶的守護,也是對強權的抗爭。
是為序
邢福增
安息年寫於國立政治大學
二○一八年「六四」廿九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