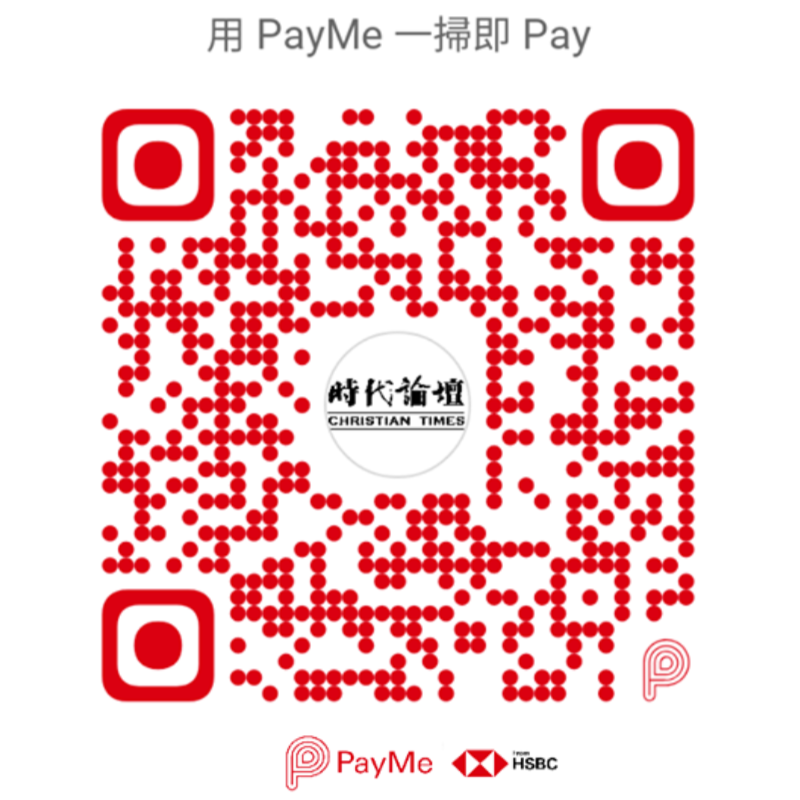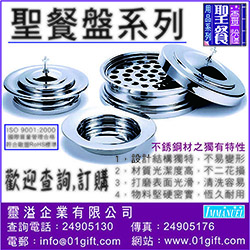进图兄自二○一七年九月开始,每周都会撰写一封信给因东北发展案、公民广场案及占旺藐视案而被牢的青年人。如此持续的工夫,需要的不仅是恒心与毅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言说的坚持与热诚。
敢问:在这个强权当道,谎言充斥的世代,言说仍有作用吗?我想起耶稣跟门徒说的一段话:「我该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们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太十一16-17)面对冷漠(indifferent)的世代,言说是否只是自说自话?
其实,沉重的无能感,什至也出现在言说者身上。目睹理想及价值的崩坏,什至连自己曾持守的信念,也有动摇的可能。正如在监狱中的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将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太十一3)新约圣经中的施洗约翰,被视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路三4)是他一生的使命所在。被牢者约翰的问题,虽不能反映他对耶稣身份的否定,但也表现出其怀疑及不确定。在迷失的当下,很容易有所动摇,这真是我要走的路吗?如果连自己的信念也不敢肯定是否真的能实现,那么,又可以言说什么?
我相信,进图兄写《给下狱青年的信》,一方面是出于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知的信念,要借着书信向这个世代言说。另方面,他的言说,并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答案拥有者自居,却是让我们看见,一位基督徒新闻工作者,如何在遭遇凶徒施袭的人生巨变中,「迎锋而立」,再次在信仰世界中,认定这个世代需要信念及持守价值。他的言说,既是与下狱青年的坦诚对话,也者未尝不是进入自己心灵世界之中,与自己、这个世界及上主对话。
记得有一次跟进图兄见面,他分享自己近日在阅读的书籍。从《给下狱青年的信》中,可见他曾引用的作家及着作什多,包括:潘霍华的《狱中书简》及《团契生活》;莫特曼的《盼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The Spirit of Life、Ethics of Hope;德兰修女的《来作我的光》;依路(Jacques Ellul)的Propaganda,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鲁益斯的A Grief Observed;Jonathan Sacks的A Letter in the Scroll;还有约翰卫斯理、古伦神父、马丁路德金、卢云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与迪尔神父(Father John Dear, S. J.),及管理学大师Jim Collins等。不少圣经人物,如约拿、约瑟、约伯、大卫、所罗门、以斯帖等,也曾在信中出现。我相信,进图兄引述这些着作或内容,是因为当他带着自己经历的问题与挣扎来阅读时,得以与作者的生命相遇。他也期望下狱青年,也能透过阅读这一扇窗,得以窥探牢室以外辽阔的天空,人在狱中,但心灵及思想却不被牢禁。
诚如多次被国家牢禁的刘晓波,在〈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1999)一文曾说: 「生活在极权制度压抑下的反抗者,尽管他的声音封杀,他的身体被囚禁,但他的灵魂从未空白过,他的笔从未失语过,他的生活从未失去方向。」这正这个世代需要持守,并且言说的信念。
其实,当我在读进图兄的书信时,也感觉到他是写给我的。无疑,我们并非身陷囹圄,但近年社会沉郁的氛围,也令人有一种被囚的感觉。记得刘晓波曾说:
我不是走出了小监狱(秦城)而又进入了大监狱(专制社会),而是一直没有走出自我设置的心灵牢房,不敢面对真实的心灵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谎言的恶性循环的终极根源。扩而言之,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牢房构成了专制社会的大牢房。因而,冲破专制主义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们自己的心狱。
是的,我们并未被囚于那狭小的牢室空间(小监狱),却是活于强权专制的社会(大监狱),还有自己内心的「心灵牢房」。
这样看来,《给下狱青年的信》,不仅是写给厕身小监狱的青年人,也是写给每一个被困在「大监狱」及「心灵牢房」中的你与我。进图兄相信,即或如此,这个世代,仍需要言说。言说我们对理想的在乎,对真实的坚持,对记忆的守护,也是对强权的抗争。
是为序
邢福增
安息年写于国立政治大学
二○一八年「六四」廿九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