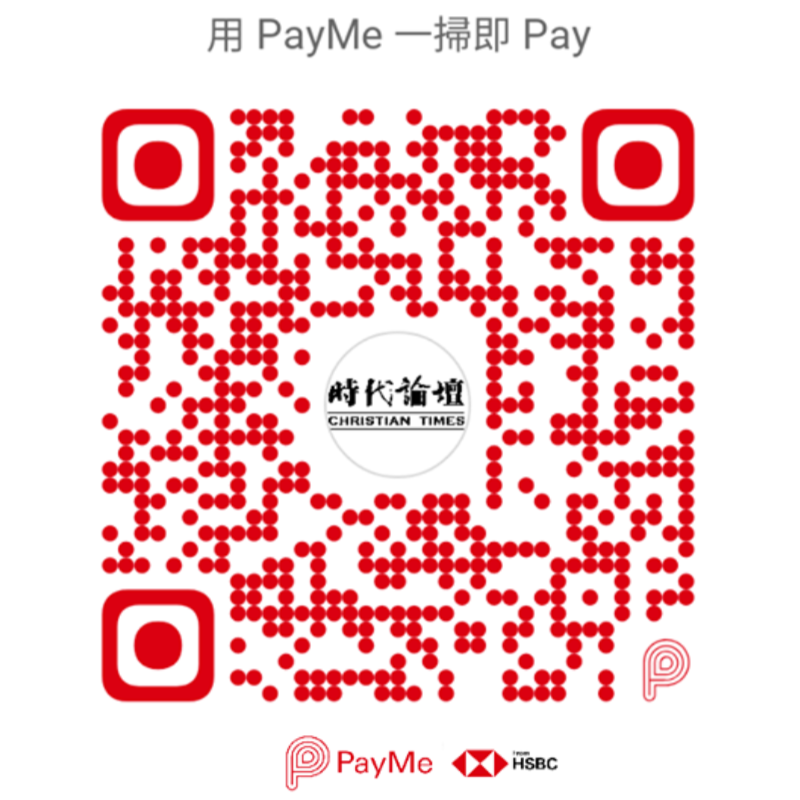打从「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以降,戴耀廷、朱耀明及陈健民三人的名字,便紧紧地扣在一起。许多人都知道,「占中三子」中有一位牧师及基督徒。有人笑言,馀下一位陈健民也是「半个基督徒」、「曾是基督徒」……
关于陈健民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他在最后一课(编按:陈健民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的公开课堂)中首次自白:「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学生问了很多年,我经常不回答。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有信仰而无宗教的人。」我们该如何理解「有信仰而无宗教」?对此,笔者于一月廿四日在陈健民的办公室跟他作了一次访谈,「其实我几十年都没有去与多人讨论自己的宗教信仰……」,听他娓娓道出自己与基督教信仰、教会及宗教间的拉扯、纠缠与连结。

信仰对我生命有很强烈的要求
中学生时代的陈健民,是一位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他是家里第一位信主的人,就读于路德会协同中学。中三那年,被一位基督徒同学领他回教会,翌年便在信义会钻石山堂受洗。由于他喜爱弹结他,常在团契中表演音乐,「感觉很安静很舒服……是音乐带动我进入教会,然后与上天有些沟通。」
教会生活改变了他的性格。自小由于声音「好沙」,令他成为「几自卑、恐惧的人」。「以前搭小巴,连『街口落车』几句话都不敢开声说」。但在教会开始与不同人说话,「你觉得他们会接纳你,你便不怕,试着去讲。所以教会对我有很大impact,这是我的起点。」
更重要的是,成为基督徒后,「开始认真去想想信仰在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要过一个更加serious的人生,对人生要有一个更好的看待,如何觉得要过得有意义,是上帝希望你去过的。我经常觉得我是上帝的器皿,但这器皿要用作什么?……我不想白白度过这生,而且不断地问,上天要我生活在这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借着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他开始寻找意义,并且得着克服困难的勇气。「若你找对一个上帝要你做的事,上帝一定加力给你,一定会做到。」
未几,这位中学生遇上了「金禧事件」,并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维园集会。「我当时真的不是因为关心社会而参与金禧事件……」,但事件却对他带来重大的冲击,「我发现自己是那么没准备进入社会,我没法判断一件事的对错是非,而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挣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这种要求令他产生恐惧感,「觉得自己无能力分析社会,亦无能力承担上天给予自己的使命,因此,那时候开始便对自己有要求,要能进到大学。」结果,他便决定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
一九八三年,陈健民在大学毕业前写了〈我的四年〉,清楚指出自己曾在上帝面前的立志:「我要读社会学。我要先了解社会,然后才能服务香港、贡献祖国……我要研究基督教社会学,我要以哲学为起点,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这是他在新生注册表上为自己订下的学习目标。(编按:〈我的四年〉文章扫描影像见邢福增〈作基督徒的意义:读陈健民〈我的四年〉(1983)〉)
在教会内我没有平安
大学的氛围,主修社会学,副修哲学,令陈健民更多思考人生与信仰,「开始有更多对信仰理性的思考,更多要求信仰要在这世界中实践」。但当他带着这种渴求回到教会时,「哗!教会对我来说,开始完全感觉是两回事,令我觉得是相当窒息、不舒服的,在教会内我没有平安。」
他参与的教会位于钻石山大磡村,是大型的寮屋区。会众由不同地方回教会,聚会结束就离开,「完全同社区没互动」。他形容有一次,参加圣诞节报佳音,「大家要搭车去教友的家报佳音,而不会在社区内报佳音」。这经验令陈健民产生强烈的感觉,原来「这间教会可以同他周边的世界隔绝」。
为了打破这种隔阂,他任青年团契团长时,便要求团友「进入自己生活的社区唱歌」。对团友而言,第一次「大家觉得很striking」,因为不少参与教会多年的人,只是「望着教会这建筑物入了去就算,周边是完全没关系」。「周围很肮脏、教会很干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曾提出希望开放教会,成为社区补习的地方,但却换来执事、教友的反对,「觉得会整肮脏教会」……
他感受到,原来不少教友只在私人问题(如升学、爱情)上寻求上帝,但对于社会问题,「又不会问上帝有什么意思」。陈健民形容,这是一种「将信仰放在『私有化』的做法,就像是把信仰放在盒子之中」,但他读圣经时的理解却不是这样:「以前的先知不是都会走到城墙和守望台之上,不断拷问上帝:『为什么祢会让外邦人入侵我们?』」
此外,陈又发现,教会「不能讨论问题」,因为「每件事都已经有一个答案」。他常常从理性出发去思考信仰,结果令牧师感到「很辛苦」。有一次,众人在圣殿追打一只老鼠,事后他真诚地问牧师:「为何我们要杀老鼠?」、「上帝为何要造老鼠?」、「若它是没价值,我们不能容忍它,上帝为何要造这生物?」陈的问题,企图从人世间的「恶」(evil)来拷问创造的意义。不过,「我的牧师『会晕畀我睇』,即是不要再问了。」他感受到,不知该如何对话,「与牧师格格不入」。「最惨的是,你还是在做团长,还是崇拜的主席,就好像你的肉身还在船上,但你的灵魂却抽离得很厉害。」
「我慢慢观察,教会大部份的人,其实是想找安歇的水边,想追寻一种安全感,你不要搞乱他们。你问这么多问题,他们其实是很辛苦。这个世界已很乱,他们只想一个简单、直接、绝对的答案,所以返教会的人是求平安的。」
终于,在大学毕业后,陈健民就离开了教会。

反省信仰,改变世界
虽然教会无法满足陈健民对信仰的思考,但这却没有窒碍他的寻索与信仰。诚如他在最后一课指出,大学时代阅读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及西班牙神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着作,对他的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潘霍华只是帮我总结有关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和信仰应该要怎样在世界实践,理性的部份是看乌纳穆诺这个西班牙神学家的作品,所以在灵性上安顿我的人是乌纳穆诺,对生命应该如何实践的部份是潘霍华。」
除了两位欧陆的神学家外,陈健民也谈及了香港神学界对他的影响。那时,他参与了学园传道会。有一次学传在道风山上有禁食祈祷会,他听说道风山上有一位神学家叫邓肇明,便特地去拜会这位在山上研究神学的人。
邓肇明问他来访的原委,后来在讨论中触及一些圣经问题。他仍记得邓说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其实是以色列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战争过程中的一位「战神」。对上帝观念的理解,往往受不同历史阶段的处境影响。「人会参与在传讲上帝的事之中,而非所有人所说的话都是上帝的说话。」这次信仰对话,给陈健民带来极大冲击,「在圣经中写的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些人在寻找上帝,那些人在书写在历史中上帝对他们来说的意义?还是说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说话?」于是,他特别修读了当时中大崇基神学组的科目,包括李炽昌的旧约圣经及郭佩兰的基督教伦理。透过课堂的讨论及阅读,开启及拓阔了陈的信仰视域,不仅在理性上更多认识圣经及信仰,更重要的是,也「影响了我怎样看社会上不同的议题」。这对他重新检视入大学时的立志——信仰如何结合生活,又有更深的体会。
为了投入生活及塑造自己,他决定参与学生会的工作。其间经历了中大「四不改三」、「五不改六」的罢课和抗议运动。对于繁重的学生会工作,陈健民深深感受到,「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怎可以只顾自己?……我的信仰在当下就在问我,究竟我对我认为『好』的教育制度有没有责任?」
陈健民是崇基学院的学生,在三年级升四年始的暑期,需要预备通识科的「专题讨论」学生报告。他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做一份对社会有贡献的功课?」那时他接触到柴湾区两所社区教会:柴湾浸信会及循道衞理爱华村堂,深受两位致力结合福音与社区的牧者(朱耀明、卢龙光)影响。由于听区内牧者常说「死得人多,成日都要搞安息礼拜」,故认为死亡率高的背后,可能涉及医疗问题。「我就用社会学研究的毕业功课来帮助他们做一个研究,加深他们对问题的了解」。由于港岛东区没有医院,故病人由柴湾送往湾仔邓肇坚医院后,如再需要施手术,又要再塞车到玛丽医院。在整个暑期中,他与同组同学致力搜集数据,特别是救护车送病人到医院途中的死亡率(death before arrival)。「我想用那个数据,再用来与全香港其他地方作比较,究竟这个数字在东区是不是较高」。最后,这份专题报告为「争取兴建东区医院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统计基础。
由于柴湾区的教会及牧者(尚有天主教海星堂的关杰棠神父)在争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令陈健民「信仰如何真正与社区结合」,对贫穷人而言,福音不是「抽象」的。「他们(笔者按:指牧者)就是为了每日受害的人去投入时间,搞一场运动,要面对铜墙铁壁,也不管被人说政治化什么都好,我目睹一个信仰实践的过程。」
从学生运动到社会运动,陈健民认定,「最基本的东西是很清晰地提供及接受『改变』」。信仰如果在世界中具有意义,也是如此。

信仰与灵性的追求与实践
自一九八三年大学毕业后,陈健民加入循道爱华村服务中心。应聘时,卢龙光问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时他已经没有教会生活,但他引用了潘霍华的话回答:“to be Christian is to be fully human”。在应学生福音团契邀稿所写的〈我的四年〉中,文首也引述了潘霍华在《狱中书简》中的话:「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人才晓得信仰上帝。」他在文末仍在问:「作基督徒在这世上有什么意义?」
这样看来,「我是一个有信仰而无宗教的人」这句话,其实不仅是描述当下的情况,更是他一路走来的信仰告白:
「我一直有跟随上帝,我不觉得因为离开了教会而减弱,我的信仰没有变弱,我还是不断在寻求每一步上帝到底想我做什么。我没有觉得我的信仰改变了,但是我肯定我无法接受基督教里许多东西……」
后来,他赴笈美国耶鲁大学进修,专注于关于民主化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我没有再有什么对信仰思考的突破,因为我在之后的关注点,开始探讨如何实践我的信仰」,特别是关于民主及公民社会的课题。回港后,他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关注及实践,未尝不是跟他以生命回应现实,并与他寻求改变的心志一脉相承。因为他深信,公民社会必须有灵性基础,什至公民抗命运动中,也不应忽视其中的灵性部份。
还记得在二○一三年三月廿七日,「占中三子」在九龙佑宁堂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的场景,特别是十字架的符号,为整个运动带出一种超越现实的价值诉求。陈健民指出,整个运动的精神是自我牺牲,这跟基督教的精神价值有共通之处。他希望能够在教会发表信念,让社会大众明白,和平占中运动并不是追求暴力。整个运动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运动,但是「灵性层面在这场运动是很重要的,它不单纯是组织,真的要有这种自我牺牲的感召。」
他坦言,社会对和平占中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基督徒在内。这令他想起郭佩兰的基督教伦理课中,「不是这么简单便指基督信仰,可以令我们对社会事件有很单一的答案」。正如电影《战火浮生》(The Mission)中两位不同实践方向的传教士。「我觉得两个都对,是因为宗教可以停在这个位,让你可以很真诚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是真诚面对上帝及自己:
「我是否真的将自己拿开,去寻求上帝旨意,放在这个时空,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基督徒;我觉得信仰能产生这样的力量就够了,而具体的判断,我觉得人有很多limitation,他会产生差异,所以我不会觉得,基督徒不是人人都需要接受『占中』,他可以觉得,这个方法不会有好结果,是否对话会好一点;什至你可能会觉得不要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很真诚去问上帝在这个处境中,耶稣在这时会做什么,去问潘霍华这个问题,我对这个答案的偏差是会接受的。」
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多人都不会问,觉得同个信仰irrelevant,觉得问这些问题有何用。」没有真诚地去反省,「就本能地认为这是『搞乱』社会」,这才是问题所在。

最后的话
站在一个学者及行动者的位置,陈健民对香港教会在当下社会的角色有何期许?「我真的没有期望过教会会做什么!」他为个别基督徒的努力而感恩,但却对体制的教会感到灰心。「我觉得香港主流教会与社会已配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什么批判的声音是从教会而来,就如天国正在地上实现一样,否则的话为什么没有批判的声音?」
因应近数月中国打压宗教自由的情况愈益严峻,他见到本港也有一些保守传统的教会及信徒愿意发声,「平安福音堂也会出声明(笔者按,指「一群平安福音堂会友」),我才觉得我未对你们完全绝望」。但是,他也感到无奈及荒谬,为何这些教会及信徒只关心宗教自由,却对其他迫害人权问题沉默?「不知这个宗教自由是建基于其他的人权?当这些维权律师的权利没有人去保护,最终一天便临到你教会身上。我觉得这些是天真、狭隘的看法。」
对于近年不少对教会绝望的青年基督徒,陈健民说:「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面对过我当日曾面对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是信上帝,并非信教会,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令信仰有障碍。我觉得我们在世上是需要不断寻求上帝的旨意,不应该因为离开教会而离弃信仰。」他希望基督徒仍然能够对上帝有信心,「作为一个基督徒便是要有这么一份勇气。我希望这方面不会受到一些组织或制度影响,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很真实的经验。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教会、信仰也不会给我们答案。我觉得要继续持着谦卑的心,继续寻求,为何要因为组织的问题而放下这方面呢?」
今年四月九日裁决日子将至,陈健民坦言:「面对坐牢,我平静安稳。」既然运动的精神是自我牺牲,他期望借此刺激大家,「问为何正常的一个人要坐牢呢?」这正是向社会传达的信息与问题,「我不可以接受现时这个制度,对人是没有平等的尊重。那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深层次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问题。」争取真普选的民主制度,更核心的仍是「灵性问题」,「到最后是回到人的尊严和尊重的问题当中……对人的价值应该如何去冲量」。他期望一群人的自我牺牲,能够让香港社会「重新警醒去想这些问题。」他想起同样经历被囚的潘霍华、哈维尔(Václav Havel)、金大中等人,「I am well-prepared for it.所以我真的是平静安稳」。
陈健民指出,很感谢一些基督徒对他的关心,为他祈祷。「有人说想按手发生奇迹,其实对我而言奇迹早已发生,在我中学时候已发生,我的生命已由水变酒。」水变酒是耶稣在迦拿婚宴中施行的神迹,约翰福音叙述的「神迹」其实是「记号」。水变酒是生命本质的改变,象征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而带来新的创造。
回望陈健民走过的路,从一位初享教会甘甜肢体关系的中四学生,到大学时代面对现实世界不同的挑战及冲击,仍致力反省及实践信仰的年轻基督徒。复在曾经令他感到失望的教会,及赋予他生命意义及勇气的上帝之间拉扯及纠缠,然后走上一条有信仰却没有宗教的道路。是的,前面的路是怎样,确无人知道。毋庸置疑,信仰确改变了他的一生。但今天这个「信仰」是否只有基督教?他是否仍然珍视「基督徒」的身份,也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前真诚面对自我,谦卑追随上帝,勇于承担生活的陈健民,其实始终如一。在当前是非颠倒、极权临近的黑夜之中,陈健民说:「我的生命已由水变酒」,正是活出真诚,勇于承担,实践生命的记号。


摄影:李志雄
后记笔者早前撰写了〈作基督徒的意义:读陈健民〈我的四年〉(1983)〉后,便相约健民兄,希望可以就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作一次访谈。访谈于一月廿四日在陈的办公室进行,谈了一个半小时,感谢《时代论坛》协助,将访谈录音誊写为文字记录。现将有关内容整理,作为对健民兄(以及其他为香港作出承担者)在四月九日裁决前的致敬。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