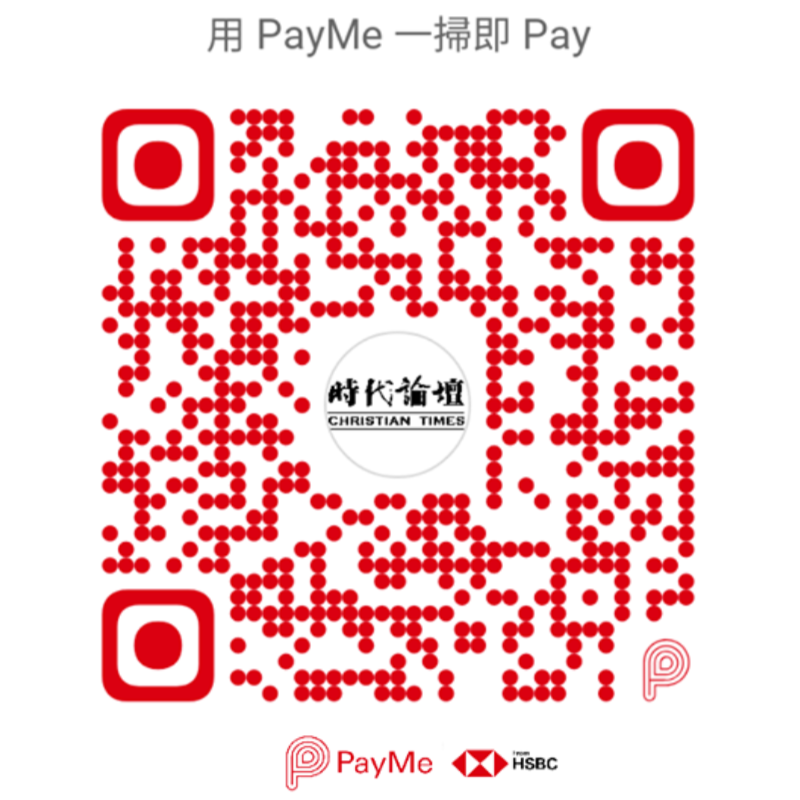四月七日一觉醒来,各个网络平台传来孔汉思神父(Hans Küng,又译龚汉斯和汉斯昆)在前一天去世的消息。自己心里先是一沉,但转念想到他早达耄耋之年,能安然在家中离去也不失为一个跑到终点的圆满结局──尤其对于一位敢于发言和饱历争议的神学家来说。
笔者不能自诩对孔汉思很熟悉,在获悉其死讯后稍稍访寻过去的相片,发现跟他的一面之缘已是二〇一一年的事,当时所服务的机构跟其创建的全球伦理基金会有个合作项目,故趁在欧洲访学期间顺道前往德国杜平根(Tübingen)探望他,报告项目进展和商谈日后计划。既然世界各大报章、教内外什或中国大陆的媒体,都已对孔汉思这位全球伦理(Weltethos)倡议者的离世有所报道,笔者对他及其思想也非专家,以下只能从一个香港新教神学人角度来分享一些对他的触觉。
宗教间缺乏理解,国际间没有和平
跟不少华人学者一样(包括非信徒),笔者对孔汉思的认识源自一九八九年,他与已故汉学家秦家懿的合着《中国宗教与基督教》。这部作品之所以引人着目,除了是因两位作者都是当时各自在自己领域的世界级学者,并且是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应该颇感陌生和意外。更难得的是,二人能敞开心怀对谈──在每章里,秦先描述中国宗教的情况,孔再以基督教角度作出回应,并且多表达理解和认同。对多数倾向保守的华人基督徒来说,最感震撼的可能是孔在后记中提出双重教籍的问题,指出这是对西方人(也应包括大部份基督徒)长期以来习惯于单一身份的挑战,却对东方人十分普遍。不过孔也清楚划分了文化、伦理和信仰上双重身份的不同层次,更由此指向「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将基督精神本土化」的议题,1这也应是每一世代信徒和教会要回应的问题。
顺便一提的是,孔汉思跟秦家懿在七十年代便于澳洲认识,孔汉思这名字也是秦为他提的。他十分喜欢这名字,一来与孔子同姓,二来汉思就是使用汉语思想,饶有哲学意味。孔曾这样说,没有中国参与的世界不能算是世界,可见这位欧洲白人学者的开阔眼光,也让人明白为何他即或在高龄之日,仍愿多次受邀前往东方演说交流。以我有限所知,孔在一九九六年起多次来华访学,成为北大的联系教授,在不同的高等学府中讲解其全球伦理概念,并与不同宗教传统的学者对话。在一九九三年,他于芝加哥跟六千名不同宗教学者聚集,并与超过二百名来自四十多个信仰群体的领袖联署《全球伦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在二〇〇九年,孔再度访京,并成为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开幕主讲嘉宾之一,有外国学者质疑大会的选择,其好友杨慧林教授半带说笑地回应,「汉思」不就是汉学吗?2八十一岁的孔当年仍兴致勃勃地游览故宫,可惜这已是他最后一次访华,之后医生嘱咐他不要再乘长途航班了,也造就了我从香港到他家里(也是其办公室)跟他汇报的机会。
大陆学界对孔汉思的重视,固然是因其倡议全球伦理不能绕过东方宗教和文化传统这一大板块,但相信许多香港的朋友也未必知道他跟我们的渊源。早于一九六三年孔便来过香港旅游,除了早年在三联出版外,当年笔者服务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也翻译和出版了他多部名着,而且他跟香港教育大学的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合作,在通识科目里引介全球伦理概念,让高中学生透过资料和活动多了解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传统,在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培养彼此尊重的精神,正如孔的名言所示:「宗教之间缺乏互相理解,国家之间就不会有和平。」这些教材和资料汇编,就是当时合作项目的一些具体成果。这计划后来更扩展至小四至中三的德育、国民及公民教育课程内,读者自己或其子女可能也是其中的受惠者呢。
对天主教会的批判精神
在以上的描述中,孔汉思之所以备受各界尊重,当然与其倡议的全球伦理攸关。不过在其所属的天主教会内,媒体讣闻对他的评价显然较为含蓄,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至他离世之日,其天主教神学教授牌照(mission canonica)仍没有恢复,以致新教朋友对他离世的反应似乎更表正面。事实上这位致力促进不同宗教文化对话的瑞士籍神父,其神学是很教会性的。十一岁便矢志「出家」的孔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可以说是爱之深、责之切,以致呈现出一种革命性以至反叛倾向,仅从其早年(六〇至七〇年代)出版的许多着作名称已可见他对教会的用心──《议会与重新联合》(一九六〇)、《教会的结构》(一九六二)、《为使世界相信》(一九六三)、《活的教会》(一九六三)、《教会发微》(一九六七)、《为何司铎?》(一九七一)、《什么必须存留在教会》(一九七三)、《论基督徒》(一九七四)等等。我在杜平根探访他时,孔送给我的其中一本书正是当年刚出版的《教会还有得救吗?》(Ist die Kirche noch zu retten?,二〇一一),足见他对教会的情怀。

(图片由作者提供)
孔汉思与后来成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于六十年代在杜平根大学为同事,二人皆为梵二时期的年轻参与者,故是惺惺相惜的同代新星。后者先成为天主教的信理部部长,即教廷的神学代言人和争议仲裁者,孔却在一九七一年发表了《真的无误吗?》,质疑教宗在其位份上不会犯错的观点,致使其天主教神学教授牌照在一九七八年给吊销。虽然他仍能保留神父一职,此后却不得再以天主教神学家身份教授神学,因此孔是以普世神学教授的名衔继续在杜平根大学任教,直至一九九六年退休。本笃十六世就任后数月,他俩曾促膝详谈数小时,但内容却非关乎教义的争议,而是全球伦理和信仰与科学的话题;在本笃十六世任内,孔也不时给予其诤友公开的批评。两年前孔和现任教宗方济各也曾有书信往来,之后他什至认为自己已非正式地给平反了,公开的澄清已不再重要,而应把注意力投放于教会和群众的未来。
孔汉思除了对圣座不能错权置疑外,对司铎的独身、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避孕问题、近年缠绕教会的性丑闻,以至安乐死等议题,多年来他都大胆地发出与天主教会主流意见不同的声音,故常被视为异见份子。这种批判精神也让他与新教神学显得格外亲和,又或许是新教思想启发了他的批判精神。孔早在五十年代末便受新教神学泰斗巴特之邀,发表改革天主教会的献议;而其在巴黎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针对称义的教义对巴特的研究,并作出对天主教的反省,这即使在今天的天主教会内也是难得的。故此他对巴特、士莱马赫以至路德等新教神学家,都能作出很正面的评价,什至能确认路德是中世纪大公神学的传承者,这从他的入门小书《基督教大思想家》(一九九四年)也可以看出。孔从这部作品发展出一本大部头着作《基督教:其本质与历史》(一九九五年),这是我经常推荐神学新生阅读的一本书,外表看似巨大,却载有许多简明绘图帮助了解神学思想历史中的种种内容;已故前崇基学院院长沈宣仁教授在其授课和着作中,也常引用孔此着中的神学典範变迁图表,3对同学掌握整个基督教思想发展历程很有启导作用。
当然,作为一位多产作家,孔汉思的着作也不会面面俱圆。一方面他写了不少针对教会教义的作品,以及如《上帝存在吗?》的哲理性经典;但另一方面在他转向关注全球伦理的阶段起,更多引介不同宗教传统并与之对话,也写了不少不同课题上的浅介,如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对一位大学教授而言,这种写作方式不免给人有点陈腔滥调的感觉。此外,这位生于瑞士琉森的中产家庭长子,相对于欧洲同辈而言也较少受战事影响,又长期在德语学术界工作,即或以敢言和受压迫者发声见称,在交往中也令一些人觉得他有点高傲。可是从笔者与他一天的接触里,亲身与这位基金会主席对谈,虽然也稍稍感到他的「气场」,但仍觉他是一位亲切健谈的长者,对于一位毫不相识的晚辈来者毫不轻视,更很高兴听到我从远方带来的消息。这对于一个八十多岁、德高望重,但身体机能已开始退化的老人家来说诚非易事。笔者仍记得孔当时虽然容易疲倦,但仍思想敏锐,跟他在工作上交流后,他更主动带我到花园合照,还把《我信什么》一书的英译本签上名字送给我留念。这十年间,间中仍听到他批评的言论和身体状况的消息,最终这位大公神学传统中的敢言异见者先行跑完他的路,守住他那种对认定之事毫不妥协的无畏无惧精神,相信这也是这时代的香港信徒应该学习的。
(分题为编者所加)

1.奏家懿、孔汉思着,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香港:三联,1989),页250。
2.杨慧林,〈孔汉思教授的中国因缘〉,《信德网》(https://www.xinde.org/show/50561; accessed 20 Apr 2021)。
3.沈宣仁,〈基督教研究与神学的多元意义──当代普世神学的进程〉,载郭鸿标、堵建伟编,《新世纪的神学议程(上册)》(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2),第一章。
作者为墨尔本神学院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