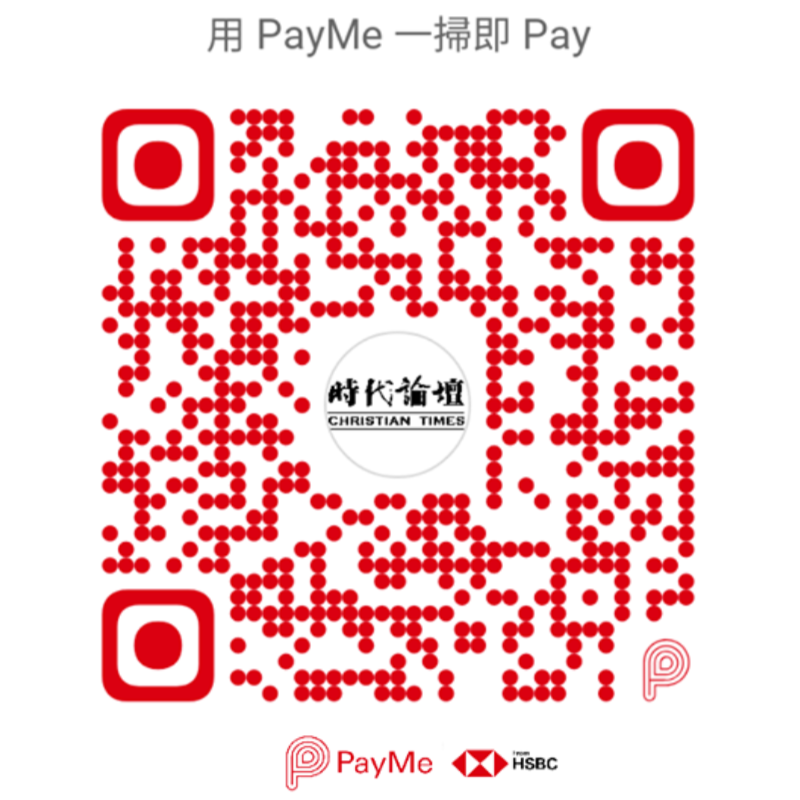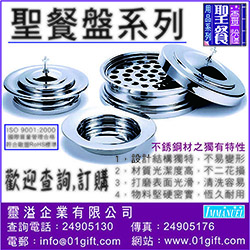前陣子我在《時代論壇》寫了一篇短文〈移居英國的潘霍華〉,似乎帶來不少迴響。我收到兩篇回應,分別是楊諾祈寫的〈離開,是為了留下的人──潘霍華在倫敦的十八個月〉以及陳家富博士寫的〈再思1933年的決定:潘霍華的抗爭策略〉。我期盼這篇回應能夠展開坦誠對話,補充我的寫作動機,讓回應者更明白我的想法,也藉此學術上討論潘霍華1933年10月離開德國的原因。因此,我的回應主要分兩個部份:一、澄清〈移居英國的潘霍華〉一文的寫作目的、限制與正確的理解。二、討論1933年10月潘霍華離開的原因。
一、有關短文〈移居英國的潘霍華〉的寫作目的、限制與正確的理解
1. 〈移居英國的潘霍華〉一文是我在《時代論壇》的專欄文章,字數限制為八百至一千字。文章的寫作目的,是透過引用「潘霍華與德國」的幾段關係與情懷作例子,鼓勵香港牧者思考留在香港的可能。因此,文章的落墨點零碎地以潘霍華與德國的片段作例子:a. 交代潘霍華1933年離開德國的原因;b. 潘霍華寫給巴特的信中最後一段對家鄉德國的無奈與感嘆;c. 巴特回信潘霍華告訴他:「立即回到德國!德國需要你!」;d. 最後引用潘霍華1939年從美國折返德國的想法:「在這艱難時候與德國的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作總結。故此,雖然以上四個片段都不太完整,卻其實都特別以「潘霍華與德國」的關係作為中心。
2. 因此,基於以上的寫作重點,也因字數所限,在交代潘霍華離開的原因上,我只集中描寫潘霍華離開德國的原因(push factor),並沒有交代潘霍華要去英國的原因(pull factor):接受倫敦教會牧養的邀請。另外,潘霍華於1933-1939年間多次進出德國的歷史,我都無法詳細寫進去──無論是1934-1935年在倫敦期間的工作、1935年4月重返德國帶領地下神學院、1939年離開德國到埗美國後折返等,我都沒有詳述。因此,感謝兩位回應者的補充,他們的補充讓讀者知道更多潘霍華的歷史。
3. 說實話,在字數有限的專欄內引用以上故事作例子,實在感到吃力,也明顯叫人誤會了我在文章要表達的意思──尤其是我對潘霍華離開德國的觀感。回應者似乎認為,我對潘霍華離開有負面的評價;其實,我對潘霍華1933年離開德國並沒有任何價值判斷。文章更從來沒有表達過「潘霍華出於恐懼離開德國」或「潘霍華離開德國就是退出德國教會戰線」、「潘霍華在外國沒有任何貢獻」之類的觀點。沒有。我從來沒有這樣寫過。
4. 我只是以潘霍華與德國的關係作類別。所謂「類比」(analogy),就是把兩種事物在某些特徵上的相似性作類比──但兩者不可能完全相同,更必然有差別。我用「潘霍華與德國」的例子類比「香港人與香港」,大概就是以「描述潘霍華離開德國的原因」、「表達潘霍華在倫敦對離開德國的無奈與情懷」、「巴特直言德國需要潘霍華」、「潘霍華最後宣告要與德國基督徒同行」,來類別「香港不少教牧離開香港」、「香港人對香港的無奈與情懷」、「香港教會需要牧者」、「香港教牧請考慮與香港基督徒同行」。
二、有關1933年10月潘霍華離開原因的討論
不過,有關潘霍華1933年10月離開德國原因的討論,兩位弟兄似乎都以共時性(synchronic)的角度來詮釋1933年10月潘霍華離開德國的原因。作為歷史發生八十多年後的後人,我們都比較容易傾向以後來歷史的發展來詮釋事情。我的意思是:究竟潘霍華於1933年10月離開德國的決定,與他後來1934年至1935年於倫敦參與「海外戰線」,有何歷史關係呢──究竟潘霍華是否懷著「打海外戰線」的理由離開德國?這正是我想邀請兩位回應者思考的問題。
我認為,「離開原因」與「離開後實踐的事」不盡相同。作為這大時代下的香港人,我深信這道理顯而易見:不少香港逃亡人士離開香港後,在境外積極參與和香港有關的國際事務,但我們不能因此說後者乃是他們離開香港的原因。當然,一個人的離開可以有“push factor”與 “pull factor” ──我們或者可以把潘霍華1933年與德國認信教會盟友的張力理解為“push factor”;把潘霍華在英國「打海外戰線」理解為離開德國的 “pull factor”。不過,我要問的是:1933年10月的潘霍華真的這樣想嗎?他在1933年10月寫給巴特的信件裡真的這樣表達嗎?由於我在專欄文章沒有空間詳細分析潘霍華的信,感謝兩位的回應,如今我可以不用介懷字數,詳細分析這封信:
1. 潘霍華於1933年10月離開德國時真的非常清楚自己在英國的使命嗎?首先,潘霍華是懷著掙扎寫信給巴特,並非如陳家富所言「在赴倫敦前就非常清楚這次倫敦之旅有著重要的使命」。當然,我們知道,日後潘霍華在倫敦對德國教會帶來不少幫助,這些都是歷史的發展後果(wirken),我沒有反對這一點。不過,問題是,對於1933年10月寫信的潘霍華來說,他真的已經胸有成竹地為著這使命離開德國嗎?信中的內容與語氣似乎不是這樣表達。誠然,潘霍華在信中處處表達掙扎,有關離開德國遠赴英國的「個人命運」(persönliches äußeres Schicksal),潘霍華曾鄭重考慮過請教巴特,向這前輩詢問意見才作人生決定。
潘霍華在信中開首寫道:「我打算六星期前就寫信給你……為何當時我沒有向你寫信呢?如今我自己也無法理解。」「我本來打算問你,我是否應該前往倫敦當牧師。我深深相信,你會告訴我正確的做法……在我的不確定(Unsicherheit)中指引我。」1 最後,潘霍華並沒有寫信詢問巴特,理由是他不想聽完巴特意見後卻不跟從。不過,他卻在信中寫道:「今天我才知道,這(不詢問巴特)是一個錯誤,我必需向你道歉。」(Ich weiß heute, daß das falsch war und daß ich Sie um Verzeihung bitten muß)。姑勿論這是否純粹禮貌之詞,但明顯地,潘霍華對於自己應否前往英國一事,非常猶豫,更多次表達自己的「不確定」,也為自己不先詢問巴特感到後悔。因此,潘霍華真的如陳家富所言「非常清楚」、「帶著使命」地到達倫敦嗎?我不認為。事實上,潘霍華在信中以「不確定」(Unsicherheit/unsicher)一詞來形容自己狀況足足有四次之多,2 我們豈能下定斷說潘霍華是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呢?
2. 潘霍華於1933年10月離開德國的主要pull factor 是牧會還是海外戰線?潘霍華在信中向巴特清楚解釋自己離開德國的理由:他一直有當牧師牧會的想法,英國有牧會的邀請,所以他就前往英國牧會。這是潘霍華向巴特解釋離開德國的第一個理由,也是他離開德國的 “pull factor”。這是不能忽視的事實。潘霍華用了三份之一篇幅,交代自己為何選擇在倫敦當牧師。相反,潘霍華卻從沒有向巴特表達自己一心懷著打「海外戰線」而離開德國──雖然這是後來歷史的發展後果(wirken)。但是,從歷史的詮釋來說,我們能夠把「發展後果」看待為「理由」嗎?如果潘霍華一心一意打算「打海外戰線」離開德國,潘霍華必定會在信中清楚以這「擁有光環的理由」作為離開的原因──但潘霍華並沒有這樣寫。甚至,我們發現,潘霍華在信中覺得自己的離開會被巴特認為是「不忠」(untreu)3。
如果潘霍華當時已經非常清楚「海外戰線」是他離開德國的理由,那麼為何他不詳細交代,這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呢?為何他還怕自己會被看待為「不忠」呢?相比起長達三份之一的「牧會理由」,潘霍華只在信末輕輕寫了短短一句:「雖然如今相隔遙遠,但我在〔英國〕教會裡卻快樂無比。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此弄清楚『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問題,我會在此繼續這工作。或者,這對德國教會會帶來一點真實的幫助。」4 作為信末輕輕帶過的一點。潘霍華説自己會參與「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是要「弄清楚」(klären werden)「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問題,但也期望這舉動會對德國教會有一點幫助。因此,「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工作,對1933年10月的潘霍華來說,只屬於「弄清楚」的試探階段,它是一個可能性。當然,後來的潘霍華可以重新定位自己在英國的角色(尤其是1934年8月參與Fanø conference 之後)。但是,回望1933年10月,當時的潘霍華真的覺得自己是要「打海外戰線」而離開德國嗎?這絕非潘霍華在信中所講的原因。
3. 巴特真的「誤解」潘霍華嗎?因此,作為回信者的巴特,並非如兩位弟兄所言,誤解了潘霍華前往倫敦的原因。所謂「誤解」,必然是針對一個文本作為「誤解對象」,在此情況就是潘霍華1933年10月寫的信。但是,巴特有將潘霍華的信「閱讀理解」錯誤了嗎?似乎沒有。如前文所言,潘霍華的信先描寫自己英國牧會的原因,之後談及他在德國認信教會面對的張力。巴特的回信,就坦言直接呼喚潘霍華回來德國更好。或許,巴特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估計歷史發展的後果──他低估了潘霍華將來在倫敦可為之事。不過,這是「歷史的誤判」,而非「對潘霍華的誤解」。與其說巴特誤解潘霍華,倒不如說是歷史的後人太快把後來的歷史結果讀進潘霍華與巴特1933年的對話中──連潘霍華自己也沒有清楚說明離開德國是要打國際戰線,巴特何來誤解呢?巴特的判斷是貫徹如一:留在德國比英國更重要。無論如何,這判斷是正確的。我從來沒有否定潘霍華在英國有所作為,我只是說潘霍華在德國更重要──無論是1935年潘霍華選擇回歸德國帶領地下神學院,抑或潘霍華1939年從美國折返的心聲,這都證明潘霍華在德國比英國更重要──這正是我前文想帶出的信息:「德國/香港需要人」,這也是潘霍華生命最後決定的存在方式。
p.s. 我同時翻譯了這封潘霍華於1933年10月寫給巴特的信,供各位讀者參考。我期盼,讀者們透過此信,更能體會潘霍華離開的心境,也對此刻的香港教會有幫助。願昔日保護德國教會的上帝同樣祝福香港眾教會。阿們。
1. 原文:"Ich wollte Sie fragen, ob ich als Pfarrer nach London gehen sollte oder nicht. Ich hätte Ihnen einfach geglaubt, daß Sie mir das Richtige sagen würden, Ihnen allein, bis auf einen Menschen, der aber an meinem persönlichen Schicksal so fortwährend Anteil nimmt, daß er in meine Unsicherheit mit hineingerissen wurde."
2. 另外3次引文如下:"Ich sagte mit Vorbehalt zu, reiste für 2 Tage hierher, fand ziemlich verwahrloste Gemeindeverhältnisse und blieb unsicher. "und das alles machte mir Angst, machte mich unsicher, ich fürchtete, daß ich mich aus Rechthaberei verrennen würde" "Daß mich das nicht persönlich verstimmt hat, glaube ich bestimmt zu wissen; dazu war auch wirklich nicht der geringste Anlaß. Ich wurde einfach sachlich unsicher"
3. "Es kommt mir auch so vor, als sei ich Ihnen durch mein Weggehen persönlich untreu geworden"
4. 原文:"Und bei alledem freue ich mich unendlich in einer Gemeinde zu sein, auch so ganz abseits. Und dann hoffe ich ja auch, daß sich mir hier nun die Fragen der Ökumene wirklich klären werden. Denn diese Arbeit will ich hier weitertreiben. Vielleicht kann man auf diesem Wege der deutschen Kirche noch einmal wirklich in etwas beistehen."
以上原文來自 Bonhoeffer, D. (2015). London, 1933–1935. (H. Goedeking, M. Heimbucher, & H.-W. Schleicher, Eds.) (Sonderausgabe, Vol. 13, p. 11-15).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33年10月24日潘霍華寫給巴特的信〉
翻譯:陳韋安
倫敦,1933年10月24日
親愛的教授:
我現在寫給你的信,其實應該六個星期前就寫的。如果真的是這樣,或者,我的人生會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吧。為何當時我沒有向你寫信呢?我自己如今也無法理解。我想,大概有兩個原因吧。我猜你當時可能正忙著一千件事情,在那煩擾的幾個星期裡,要你處理別人的生命選擇,似乎實在顯得極不重要,我自己也覺得我的事情還沒重要到要寫信給你。第二,我感到自己心裡有點焦慮(Angst)。我知道,假若你對我說了某些話,我應該要跟著做的,但我卻想保持自由;因此,我就把自己抽離了。今日,我知道,我做錯了。我必需向你道歉。因為我這「自由」的決定,是罔顧了你的自由。我本來打算問你,我是否應該前往倫敦當牧師。我深深相信,你會告訴我正確的做法。唯有你,還有另一個人,長期參與我個人的生命選擇,並把我從不確定(Unsicherheit)中抽出來。
我一直都想當牧師──我以前幾次跟你提及過。七月的時候,我得悉有關倫敦牧會的事。我帶著保留應承過去觀察兩天,得悉該教會似乎長期沒有人牧養,但我仍不確定。我應承他們會在九月的時候作最後決定。他們要求的承諾是輕省的──半年前提早通知解約。我只需要向大學申請休假。究竟我能否與這間教會建立堅固的關係,我至今仍未看得透。同時,我得到柏林東部一個牧職機會,這是可以確定的。但普魯士(Preußen)突然頒佈《雅利安條款》(Arierparagraph),而我知道,如果我被差派往那地區的話,是不會被接納為牧師的──除非我放棄對抗教會的立場,除非我甘願把自己的教會在信仰上搞得亂七八糟,除非我甘願放棄與猶太裔基督徒同行──我的好朋友正是這班人之一,他此刻沒有任何前景,他也會跟我來英國。
因此,我只剩下「大學講師」與「牧師」的選擇,而在普魯士當牧師是不可能的。我如今無法向你逐一衡量這些選擇的好處與壞處,雖然我其實仍然無法衡量,甚至可能永遠也無法衡量。我希望,自己不是因著厭煩教會的局面作選擇,也不是因著自己對我們同一夥人的立場。或者不需要太久,我就必須與我的盟友正式分道揚鑣──我相信,他們反對我去倫敦的聲音比贊成的多。如果一個人要為自己離開的決定製造一個理由,我想,其中一個強大的理由就是,曾經在我心裡浮現的問題與承擔已經不再生長了。我感到,我與自己的盟友難以形容地處於一個極度對立的關係中,我面對著一個孤立無援的處境,雖然我與這些人保持近距離的關係。這些事都叫我感到焦慮(Angst)與迷茫(unsicher),我害怕自己錯誤地變得固執(Rechthaberei):因為我實在找不到任何理由,覺得自己比其他正直、良善的牧師看得更正確、更獨到──他們都是我尊敬的人。所以,我在想,或許是時候,讓自己走進曠野一段時間,找一個牧職工作,盡可能簡單一點。對我來說,在這個時刻多一動不如少一動,這樣危險比較少。所以,事情就是這樣了。除此之外,另一個徵兆就是我用心擺上的《貝塞爾宣言》(Betheler Bekenntnis),似乎幾乎沒有一個人明白。我相信自己能夠清楚分辨,我沒有把事情個人化,我實在沒有任何原因這樣做,我只是純粹真的感到迷茫(unsicher)。
我起行前十日,收到教會辦事處(Kirchenkanzlei)的電話,説我出發英國正製造一些麻煩,因為我對德意志基督徒教會(Deutsche Christen D.C)的反對立場。幸好,我有機會與穆勒(Ludwig Müller)交談,我跟他説,我可以從此不再回來,我情願逗留在這裡,也不想升起錯誤的旗幟,我甚至在外面不用代表德意志基督徒教會。我的請求都被一一處理。穆勒做了一個難以言喻謙虛的表情,鼓勵我說:「我已經開始安排幫你清理困難了。」不過,他對我來英國的事依然不太確定,我希望最後辦理的決定是來自外面的,而且過程是快樂的。翌日,我收到消息,告訴我可以出發了。他們對「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恐懼──真麻煩。
現在我在這裡已經第八日,每個星期日都需要講道,幾乎每天都收到來自柏林有關事情狀況的消息,這都叫我幾乎心碎。如今,你快到達柏林,而我卻不能在那裡。我感到,我的離開或者會讓你有「不忠」(untreu)的感覺。或許此刻你不能明白。對我來說,這卻是一個極大的現實。雖然如今相隔遙遠,但我在教會裡卻快樂無比。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此弄清楚「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問題,我會在此繼續這工作。這或許能對德國教會會帶來一點真實的幫助。
我暫時也不知道,自己將會在此留多久。假若我知道,對岸需要我甚麼的話...... 我們實在難以知曉,我們應該做甚麼。「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但......」(歷代志下二十章12節)。
所以我就寫這封信給你。這都只是我個人的事情,但我卻想讓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再次聽到你的話就太好了。我衷心多謝你──多謝你所作的,我們一同渡過的,不能一同渡過的。你可以坦白地寫出你的想法給我嗎?我想,我能夠接受嚴厲的言辭的,並且感謝之。當我的打字機送來時,我還有事想寫信給你。這或許對你來說太沉重了。
衷心感謝你
此致
迪特里希 潘霍華
守護自由空間,請支持基督教《時代論壇》
可選擇:📲 PayMe 或 💳 網上捐款(信用卡)或
⚡️轉數快FPS +852 51100803(註明奉獻,如需收據請附姓名及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