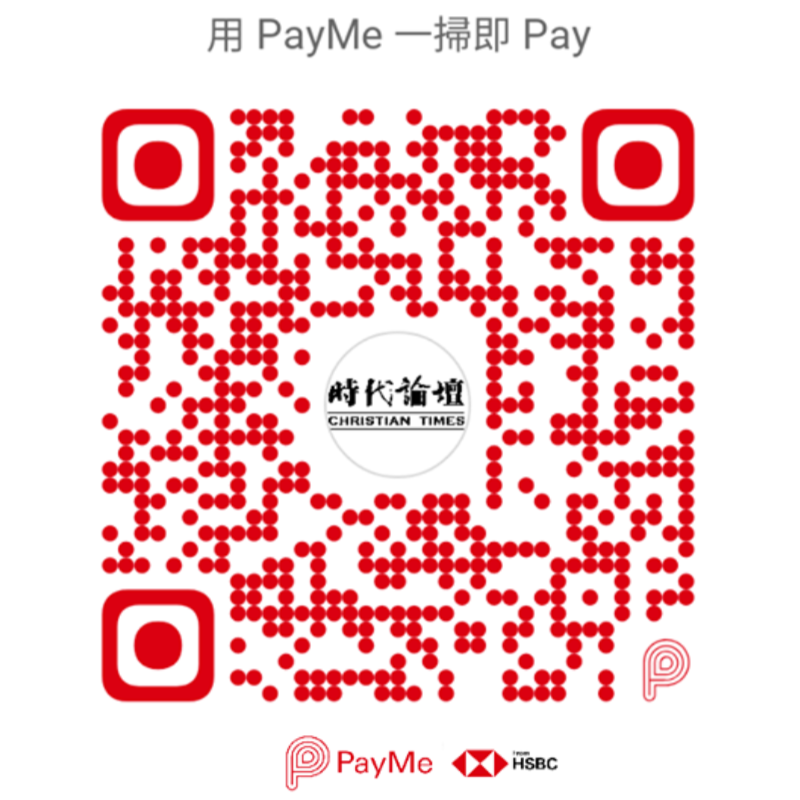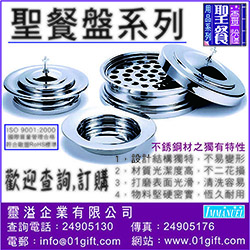二○○○年度的立法会选举期间,同志团体争取了四十八位候选人签署五条「同志政纲」,其中二十位胜出者(占立法会三分一议席)表示会为同志社群争取权益,包括该政纲的「同性伴侣应享有与异性伴侣同等之权利」,「中、小学的性教育课程应包括不同性倾向的主题」。不少议员跟随社会形势高调支持同志;可惜,至今仍没有一位「亲同志」议员在这方面的言论显出优良的议政能力,纯粹一面倒的附和而已。
香港正如其他国际大都会,免不了出现「反性倾向歧视」的同性恋人士的诉求;但比较西方社会的议员、官员、人民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反讨论、是非探究、利弊衡量,香港社会是近乎盲目地只认同西方的支持同性恋的言论,无视抗衡的意见,就如同性恋权益向受重视自由的美国,近年调查皆显示约半数国民甚至赞成立法禁制同志婚姻,且人数在上升中,只是一些政客或法官运用其地位力撑同志诉求。
教会界一直对同性恋有关的法律诉求非常关注,原因不纯是宗教、道德方面,亦包括多方面的客观因素,玆综合如下:
一、道德缺堤危机:若本地「亲同志」的法案再出现且被通过,香港势将随着西方不少国家或地区,面对同志进一步的诉求,直至他们认为完全平等为止。加拿大安省省议会曾於一九九四年辩论是否通过「同性配偶」法案(还未到进一步的同性婚姻法案),当时议员便须考虑即时要修改相关五十六条的法律,涉及家庭津贴额、儿童领养权、遗产继承权、租屋权利、性教材内容等,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结果没有通过此一法案,反映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另一方面,若本港为同志运动开绿灯,很多自称为「弱势社群」亦将高喊「平等机会」、「不容歧视」的口号,争取立法或政府拨款,迫令及教育公众接受:乱伦、群婚、换妻、娈童、人兽交、偷窥、降低合法性交年龄、近亲通婚、女性公众场合裸露上身等等(这些在西方已陆续出现)。法律作为社会伦理秩序的第一綫「把关」,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客观的公众谘询、各地的详细考察而随从飘忽的民意(正如理工大学在赌波规範化後,调查发现百分之五十五点九市民「认为赌波是赌博活动」,与两年前的百分之一点七相差极大),是对不住承担我们结果的儿孙一代。
二、性倾向的正确理解:「宗教、家庭」是「政府、法律」不容随便冲击的体制,因为宗教与家庭比後两者更早扎根在人类社会,当受尊重。根据主流的宗教传统,惟有「一男一女结婚」才可组成具延续人类能力的家庭,好让父母悉心培养社会下一代;在人类历史中,亦可印证此类型婚姻下的家庭带来社会最大裨益。因此,我们拒绝以「性倾向」为理由就可予结婚,亦质疑「反对同性可组织家庭」的言论构成歧视,理由是:
a. 同性恋并非正常:坊间常引用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於一九七三年取消同性恋及其行为是病态(mental disorders)的讲法,是不明底蕴的;因为在当年该会大约二万五千名会员中,约有一万人投票,其中虽有六成认为同性恋属正常,但占少数、专研同性恋问题的会员,大部份仍认为属病态,只是票数不及并非深究这方面的大多数会员;而在该会一九七七年的再次调查中,有七成会员仍视之为病态,一成多表示不肯定。不少学者,包括该会在一九七三年的董事局成员Dr.Charles Socarides,认为那次是仓卒的投票,是支持同志的组织(National Gay Task Force)在会内、外大量游说的结果,是政治性多於医学(科学)性。自此,同志、亲同志人士藉传媒之助,将同志是「正常」的观念做成既定事实,向公众、政府、官员继续游说,争取正常人的基本权益,而将不认同他们的人士的意见(其实大多是温和合理的,只有少数的言行是激烈的),一概归入「歧视」的罪名。
b. 性倾向可以改变:近年坊间流行称「性倾向」为天生不能逆转,且分其为三类: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事实上,今天不少治疗同性恋的个案,已证实同性恋是可以「医好」的,且成功率达三至五成,比某些心理精神病的治愈率更高。二○○一年五月九日,有公信力的CNN、New York Times 及Washington Post大事报道於上述一九七三年领导精神病学协会的专家小组,废除「同性恋是病态」的主脑Dr. Robert Spitzer的新发现,他声称研究发现百分之六十六的男同志与百分之四十四的女同志寻求治疗後,取得良好的异性恋表现(good heterosexual functioning)。Spitzer已将此研究於同年该会年会发表,并要求会方不应继续压制业内施行「转变性倾向的治疗」(reparative therapies),反对「同性恋冇得医」论调。认为「同性恋不是天生的」的例证还有很多,我们认为,既然专业权威人士都对此未有定论,外人就断定同性恋乃不会改变的天赋人权,将之与真正属於天生不能改变的种族、肤色、性别等权利看齐,是伪科学说法。
c. 同性性交应受非议:既然同性恋属先天或後天、本能或习染,在医学上、科学上一直未有定论,所以藉「性倾向」为由的立法理据并不充份。况且,有大量研究显示同志成因源自破碎家庭或挫折的求偶经历,正与现代社会吻合,容让他们乱闯同性恋情之路非社会之福。再者,有资格评价同性恋的不单是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等的专利,各大宗教亦有权就同性恋及其行为作出教义上的评价。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提出的「同性恋性行为有违生理结构」也是合事实和合情理的,其教导公众拒绝这类性行为(因易导致性器官损伤从而感染疾病,美国八成严重性病者涉及这类性交)也是合乎科学卫生和大众利益的。
d. 同性恋不宜宣扬:同志诉求基本上是性操守的问题,现行法例只将成人私下进行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所以其在性方面的法律权利仅属负面的容许,而非正面的保障(如夫妇的房事)。因此同性恋及引申而来的性行为不宜扩大至公众领域中予以肯定,如要求学校性教育课程正面教导同性恋欲,要政府资助城市办同志节庆让他们性感地游行,要商场刊登宣示同性恋性爱的海报等,这都是过份要求,美化了一项「未算犯法」的不当行为。然而,除性爱活动外,我们肯定同性恋者在生活各方面拥有一般人的权益。
三、同性恋不属人权:基於以上理解,我们认为同性恋行为不是基本人权,只能视为生活方式。我们虽然不认同某些生活方式,只要那些人愿意负责自己行为的结果,我们就不排斥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但用公众税收去资助某些人过自己喜欢的特殊生活方式是不公平的,用立法的途径协助某些人获得没有付出代价的权利是一种特权(如同志要成为夫妇却没有能力为生产社会下一代作贡献,就算准予领养也是剥夺该孩子受异性父母教养的权利)。非一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受到滋扰,正如香港目前情况,不宜获得法律的保障;否则很多另类生活方式的人,都可要求法律保障。
我们肯定人权的重要,因我们相信人非同动物,人拥有灵性,且在神权之下获赐人权,有规有矩地享受合乎人性需要的生活。然而,权利若无限制地扩展,享乐若超越人性需求,则人类社会将会陷入混乱,非人类之福。同性恋被称为人权乃是误用人权。
a. 限制同性恋并非霸道:既然同性、双性恋爱是不合常理且可以治疗的(参第二点),则同性恋、双性恋发展到有性行为更应受劝止,但我们并非剥夺这类人士的基本人权。同志群体在教育、医疗、住屋、工作、娱乐等基本权利上不应与异性恋者有别。然而,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个人、群体的权益不应侵犯其他个人、群体的权益;大家在各自範围下自由活动,但亦容许彼此表达不同意见。大部份社会都有由大多数人持守的传统主流价值观,只要这类人士没有压制少数异见者,不应被视为道德霸权主义者。我们不认同香港存在异性恋霸权者,因为今天香港并没有团体组织在言行上倡导剥夺同志群体的基本人权。有市民提出不选亲同志的立法会议员,只属选举文化下的选民选择权利,不能与打压、歧视同志混为一谈。
b. 彼此限制乃社会常规:法治的香港已日益重视本地同志社群的基本人权。然而,我们忧虑当下社会讨论的「性倾向歧视」,只是令同志由弱势变强势,走向另一极端。人权受限制是自由社会的常规。兹先举数例阐析:同志租屋独立居住不应因其是同志而不获租赁,但同志租房则可因屋主认为其行为可能影响同屋的子女而拒租;同志有平等机会找一份合其资格的工作,但某些不认同同性恋的办学团体可拒其任职教师;同志要捐血,但红十字会要保障公众而捥拒之亦合理;成年同志的性行为虽不牴触法例,但宗教团体可给予此类会友纪律处理(这并不违反宗教自由)。以上每组例子同出一辙,就是个人权利若进入别人範围,别人也有权接纳或拒绝,因其权利的实践若介入别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经济利益等的时候,也应受到别人的同意与否所限制。
对应以上例子,自由社会中存在不少解决之道,如:同志可找好此「道」者租房,可向接纳同性恋的教育机构(如家计会)申请工作,更可自办捐血机构,自组「同志教会」。在多元自由的社会中,影响他人的同志生活虽会受限制,但出路却不受限制。我们认为若「立法要别人必须接纳同志诉求」,只会制造同志成强势社群。
四、更多人比同志更有理:或许有人说同志争取的只是公共资源、政府政策、法例准则方面与公众同获「平等」机会。然而,比同志人口更多的其他各类「天然身份」人士更有理由要求已失去的「平等」权利¾ 如肥胖者一直不获飞机、巴士为其设特大座位,矮个子不获纪律部队降低入职高度取录他们,其貌不扬者非因能力被拒於很多工作,说话带口音者常遭人排斥等,这些才真是歧视。再者,若同志享有减税、住屋、遗产等权益,那麽相依为命的单身兄弟姊妹、挚爱朋友更应有此等权益了。如何才构成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复杂且牵连甚广的课题,亦并不一定同志的处境比其他人士须先受理。「有求必应」的立法态度亦容易为社会上制造很多滥用法律呵护的特权阶级,实属不智。
五、同志多属性放任:若从理论争拗进到现实数据看,则更可信的是:同志是「性放任」多於「性倾向」。从多年来各地各类的调查中,均发现同志群体的性伴侣数目(尤其是男同志)远高於一般人士,这是不争的事实。早於七十年代末在三藩市调查并受重视的Bell & Weinberg Study已称,男同志中百分之廿八一生有一千位以上性伴侣,百分之四十三有五百位以上,百分之七十五有一百位以上,八成称其一半的性交对象是不认识的;仅少於百分之十男同志有较持久委身的关系。虽然本港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但只须稍加观察,男同志间的接触以「性行先、爱行後」是极其普遍,而一位本地争取同志权益的男同志就公开声称自己八年来的同性恋生活已有二百位性伴侣。本港迈向西方式国际都会,随之而来的性开放似乎是趋势,但不等於对我们社会有益。
六、性放任宜受约束:自由的社会容忍而不谴责性放纵、性随便、性活跃的人士,但若进一步修改法例保障各类「性放任」人士享受其生活方式,可以任意结婚离婚、领养子女(包括异性恋者),是否与「夫妻之道所要求的终身相许」、「孤儿在被安排甚麽人领养方面应受法例保护」的社会共识背道而驰呢?本港同性恋运动一直离不开西方同志先行者的议程,而芝加哥於一九七二年(此运动的早期)曾在同志大会订下运动的长远目标,包括「多人同居合法化」及「成人与儿童性行为合法化」,此等逐步出现的「婚姻」诉求实在值得本港关注。我们及不少人士对婚姻定义的修改及领养儿童资格的放宽存在忧虑,绝非杞人忧天。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讲场,二○○三年九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