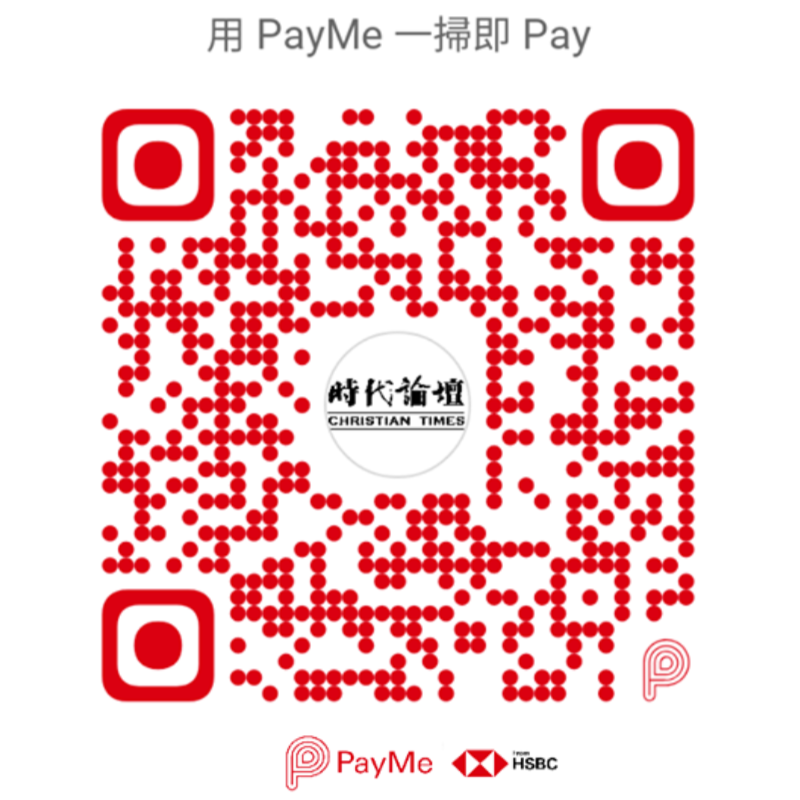十六日(上月)星期天,當我匆匆趕到醫院時,母親已離世,在上帝的懷裡安息,我的老戰友就這樣平靜安詳的不辭而別。我看著那躺臥軀體,如此陌生,但又卻曾十分十分親切。這麼多年,我總覺得自己的母親不會離開我,我們太習慣彼此的存在,所以當我確切知道她靜靜遠我而行時,我的表情不能表達我內心的萬分一感受。這一天真的來了。我的老戰友放下她疲累的身軀,她要我獨個兒上戰場。她行的路行完,她當做的事也完了,我只好學她從前拖帶著我們一樣,牽著我的小兵哥踏上從前我們曾行的路。這路有時平平無奇,不時驚濤駭浪,但缺了妳,媽,這路不好走。
有商量,有相爭
我與母親相處四十多年,母子倆有商量也有相爭,不過,有很多合作的時刻,比如她在尖沙嘴為上海的酒吧媽媽生當傭工,我住在那裡也就是半個傭人,她煮菜,我為她洗盤碗,她掃地,我幫她執床,星期天我全職為老闆孩子燙衫褲。家裡缺錢,她會教我到她堂姐妹處籌十元八塊,途中買米回家,我吃了大半份,她就微笑,忘了這錢要還的呀。一段時間,為了增加收入,我們在佐敦道的佐治公園擺小檔。她削皮串穿,我則扛著透明水盤,沿路叫賣,夜靜母子倆數錢時,頭上的月亮特別清明,有時她在西餐廳當洗碗,老外不愛雞髀肉,她煎熟給我吃,我仍記得那生鏽的拱圓鐵器,內有三四件別人吃剩的西餅,我眯上眼享用時,她的笑容令我醉心,我右手還撕扯著嘴裡的雞腿時,左手已執起另一份,她就笑得更開心。某夜,我內耳生瘡,整夜不能眠,她揹著我唱歌直到到天明。
還有,我們初到香港時,她曾帶我到土瓜灣的露宿者之家住過一夜﹔我曾經寄宿,她轉告我,我自己曾說過但我忘了的話,比如我曾說:「媽,昨夜打雷,我嚇得彈起床,我叫媽媽,媽媽你在哪裡。」我母親邊說邊流淚,我的恐懼早就忘了,但兒子的驚惶卻刻在她心深底處。她曾在旺角某薦人館工作,我喝完汽水,吃一個蛋撻,然後帶那些傭人到九龍塘豪華公館見工,她常說我是位好幫手,但卻不喜歡讀書。有次她輕描淡寫談到。第一天上某家做傭工,主人引她入廚房,然後反鎖著她,夫婦倆去就餐,為怕她會偷東西。她第二天就辭職不幹,我年紀愈長,這故事常常刺痛我,直到今夜。
小時候沒有機會進西餐廳,但茶餐廳的刀叉卻有西洋味,所以特別喜歡母親帶我到茶餐廳去,代價只是替她挽餸菜,我便可亂點A、B、C餐,到她回來,臉上露出狡黠的笑容,我知又打了一次頗重手的「斧頭」,我又再多點一兩個菠蘿包,我們心靈相通,見她沒有責備我,更深信她做了手腳。
我媽可不是好相與的人,她並不溫柔,有時亦暴躁,但頗疏財,有段時間,她因工作壓力,神經衰弱,即現今的情緒病,休息了一段時間,我只好寄居在她堂妹的舖頭的閣樓處,我那時已是中五生,理論上已可出外做工,但她不鼓勵,不過她聽到我堂姨說我的閒言閒語,她二話不說,用一條長擔挑把我的細軟扛在肩上,由油麻地行到尖沙嘴,我在她背後跟著,覺得扛擔挑老套,很不屑與她同行,那段路,她一人吱嗦吱嗦的在走,就因為受不了別人的氣。這段身影到現在還讓我自己疚愧。就這段路,我不在距離上離棄她,而是我背棄了我戰友,媽,今夜我要向你道歉。
千金小姐當女傭
母親生在一貧困之家,被別鄉的人領養去,但竟由貧家女而成為千金小姐,她哥哥比她年長多,很疼愛她,哥哥畢業於廈門大學,對妹妹的教育就很著緊,難得有讀書機會,不單中學畢業,還上了縣的師範學院,但也為婚事,應該沒有畢業,但那年代,在農村寫得一手好字也沒幾個。她性格強悍,在夫家也就不太受歡迎,但因著學歷高,哥哥厚愛,夫家只能將就將就過日子,後來也是在她催促下,我爸爸到廣州闖,解放後省政府動員農民回鄉,我爸爸哭著等遣回,我媽卻怒把歡迎的紅花球掟到屋外,堅決不走,後來想想見勢色不對,便獨個兒到香港探路,然後接我們一個一個來香港,我爸爸是孝子,留在廣州侍母,廿年後才能一家團聚。我媽受她哥哥影響,知道知識可以改造命運,亦令她有較高的視野,務必把她的孩子弄到香港,沒有她,我的命運定必要改寫,我有幸在這殖民地成長,逃過了當時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媽從沒要我工作養她,只要我繼續讀書,她就滿足。直至我當上導演,她仍在一藥房為人做飯,她喜歡花自己賺的錢,直到六十多歲才真肯退休。
一位農村的千金小姐最後要當住家傭工,受氣被差使,又要為我操勞,但她走過一波又一波的困境,這不單她自己的困境,也是香港的困境。當貧困在香港是常態時,她自己捧著那本《自學英語不求人》學習英語,好等她老闆的客人打賞,為了孩子的前途,來到香港這陌生之地,從頭而起,幹過打石工人,做過包屍阿姐,從小姐變媽姐,從小販到清潔工人,想起她叼著煙,買狗、買馬、搓麻將,有時被事頭婆無理辱罵,她眼裡迸著怒火,那副誓不低頭的模樣,咬咬嘴唇也就吞下那份恥辱,她以同情讀書比她少的人為自慰之道。
我太太以為她老人家喜看大戲,要為她購票。她卻搖頭,因為她喜愛的電視節目是賽車、拳擊、足球等,是她第一次帶我到花墟看足球比賽,至今我仍是足球發燒友;是她放我在茶餐廳等候,數十年後「表哥餐廳」包含我對母親的思念﹔是她帶我到這裡生活,為我的前途設置了一個自由的空間,一個讓我馳騁的國度。我從未聽過她唉聲歎氣說自己命運不濟,我聽到的只是她向艱苦的生活咆哮:她沒有顯赫的事業,於我而言,她卻是一個偉大的企業家,因為她造就了我,我也不是一個成功人物,但母親對我的愛護,使我頗單純的認為人間有情,我對朋友的關切,對家庭的愛,都源自她,她的後代,一家廿多口,也要感謝她當時的決定,因她帶我們到一個可以自主自己命運的地方。我們今天生活得妥當,就是她當年一念之間。
把一切留給媳婦
我母親一生不信風水命理,也不入廟參神,她不信塑像可以打做自己將來。四十年前她受浸成為基督徒,是她帶我到教會,到我因情緒病而在人生低谷時,適時向上呼求,這呼求的種子,也是母親在四十年前為我種植。
我與太太坐在沙發上,她對我述說我在美國時,奶奶捲著被鋪鋪蜷弓著身在沙發上睡,陪她,怕她寂寞。有時夫婦間爭執,太太說奶奶必定在她面前數說我的不是。她有一百元她必定花九十九,讓太太開心。她生前還對我姐姐說她所有東西都只留給我太太,她沒有留下可以用金錢量度的東西,她的遺產,誠如我太太說﹕「她愛你,所以也愛我。」對,愛就是衡量世間一切的最高標準,那怕是任何政治制度,任何道德哲學。我們夫婦倆坐在軟綿綿的布椅上,紅著眼追憶她生前的點點滴滴……最後兩三年,她患上癡呆症,神色逐漸衰竭,連我也不認得,前些日子,當我在人生幽谷時,我打開她的房門,極想尋求她的慰藉,但我亦知她已有癡呆症數年,能認得我也不錯了,誰知她望著我,溫柔的問:「你的病怎樣了?沒事不對嗎?」為了對兒子的關愛,她的意識在停止運作前拼命的湊合這兩句話,驚天泣地,聲弱情濃,這是我老戰友最後對我說的一句安慰語,自此她望我的眼神迷迷惘惘,直至離世。
媽,你在天國平安嗎?要不要聽聽你孫兒在追思夜為你唱的輓歌。
「無論是住在,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臥在,陰暗的幽谷
當你抬起頭,你將會發現
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雲上太陽,它都不改變,縱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它總不改變,哈哈,它不改變」
(本文原刊於《明報》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世紀版。本報獲作者授權刊登。)
(第八五○期,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